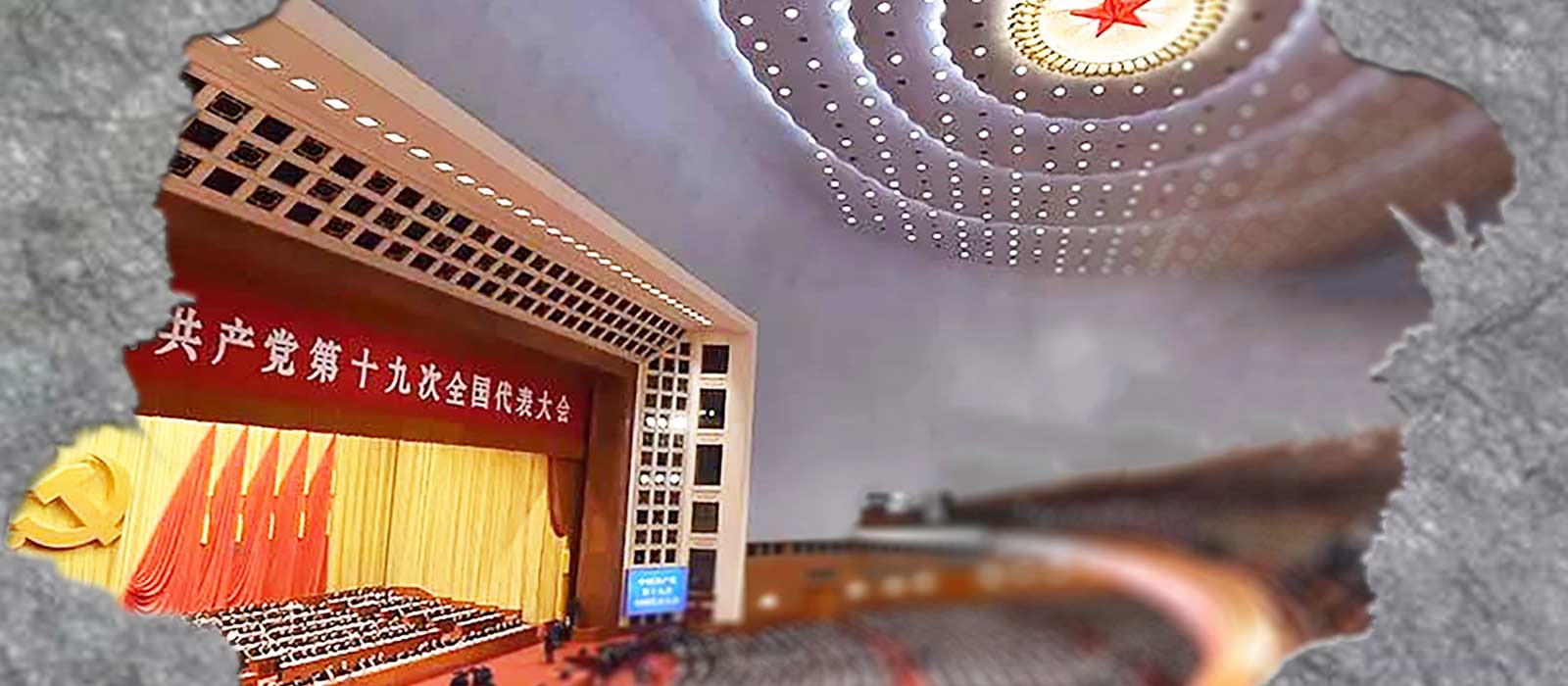「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言令色」,指言語巧辯、態度奉承。「鮮矣仁」是「仁鮮矣」的倒裝句,謂「很少是仁者」。孔子主張講話要負責任、對得起良心,因此要「慎言」,如「敏於事而慎於言」(〈學而〉)、「多聞闕疑,慎言其餘」(〈為政〉)。但「慎言」不是「不言」,因此該說話時就要說,否則「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季氏〉)。由於「慎言」之仁者通常不會舌粲蓮花,因此很少表現為「巧言令色」。所以凡是看來「巧言令色」者,很少是仁者。不過,「鮮矣仁」並非「皆不仁」,因此仍可能有例外而被我們誤判。反之,〈子路〉篇中,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亦未把「剛、毅、木訥」者直接視為「仁」。可見「巧言令色」和「剛、毅、木訥」都只是外顯徵候。究竟其人「仁」否,還是要看內在用心。
「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說:「我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
「為人謀而不忠乎?」
三件事中,第一件事就是「為人謀畫,是否盡忠?」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衛靈公〉),故必先志同道合,才有「為人謀」之可言。因此,此處之「為人謀」,絕非「為別人謀利(或名、權、位…)」,而是「為『彼此共同信奉的道』而謀」。說到底,所謀者仍然是自己內心信奉的道。故曾子所問「為人謀而不忠乎」,絕不是問「有沒有不忠於對方」,而是問「有沒有不忠於(自己與對方共同信奉的)道」。曾子深知孔子視「忠」為「忠於內心之仁道」(大忠),故以「忠恕」釋「夫子之道」。而朱熹以「盡己」釋孔子、曾子之「忠」,可謂抓到要害。明乎此,則知曾子此處所問只是「自己是否盡心」,而非「他人是否滿意」。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第二件事是「與朋友來往,是否守信?」《論語》屢言以「信」事友。《禮記》〈學記〉云:「大信不約」,可見儒家看重的「信」並非「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小信」。儒家所守之「大信」,仍是儒者內心基於仁道所許之願,而不是與人約定的表面文章。因此,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諒」者「信」也,就是主張堅守正道而不顧小信。孟子亦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離婁下〉),也是此理:為了「義之所在」,可以「言不必信」。
「傳不習乎?」
第三件事是「老師所傳之道,是否做到每日反思溫習?」《論語》中「傳」字兩見。除此處外,即子游批評子夏教學之法,子夏反駁時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子張〉)可見「傳」專指老師向弟子「傳」道。韓愈〈師說〉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係將「傳道」列為老師之首要任務,確為孔門正宗。「習」即「學而時習之」之「習」,是反思而非單純記誦。「傳不習乎」,就是說:老師所傳之道,必每日反思之,以求日益加深領悟。」
「忠」、「信」之分
儒家的德目裡,「忠」是對己,「信」是對人(君上、朋友),而「習」則是對師(所傳之道)。此外,「孝」是對君上、父母,「悌」是對手足。但都要以內心的「仁道」為準,不是無條件地、不加反省地「愚忠」、「愚信」(前引「大信不約」,故不應拘泥於錯誤的約定而違仁)、「愚習」(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因此若自省之後,覺得老師所教不合仁道(自己的良心),則必爭之,不可盲從)、「愚孝」、「愚悌」。因此,儒家德目的核心價值是「仁」,其他一切德目都以「忠於仁」為前提。而儒家的「忠」之對象,不是他人(國君、長官、父兄),而是自己內心的「仁道」。說成白話,「忠」就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儒家而言,所有的倫理(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道理)都必須首先「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凡事先捫心自問(摸著良心問問),就是堅持自身「道德的主體性」(「道體」,相對於「器用」),所以君子當然「不器」。
這種「忠」、「信」之分,在春秋時期原是君子間的共識。據《左傳》記載,西元前607年(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不像個國君),…宣子(趙盾)驟諫,(晉靈)公患之,使鉏麑賊(殺害)之。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刺客鉏麑受晉靈公之命而去暗殺趙盾,當他發現趙盾是晉國百姓的好領導後,面臨兩難困境:他若不執行君主之命而放過趙盾,只是對君主失信;他若執行君主之命殺了趙盾,反而是不忠。可見春秋時期的「忠」,決不是忠於個人(君上),而是忠於原則(仁道)。所以說「忠」是對己,「信」才是對人(君上、朋友)。「忠臣」是「以忠事君」之臣,而不是「忠於君」之臣。
儒家的「忠」,首先是忠於自己的道德信念;因此真正的「背叛」,不是背叛君上、師長、父母、朋友,而是背叛自己的良心。由此可見:中國人對「罪感」體會極深。中國人所謂「恥」,是因對不起自己的良心而羞於見人,是由「罪」生「恥」。西方人類學者將日本文化定性為「恥感文化」(相對於西方基督教傳統下的「罪感文化」),固然正確,但擴大到中國儒家,以為儒家也如日本人一樣欠缺內在良心、只有「恥感」而無「罪感」,則是淺學謬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