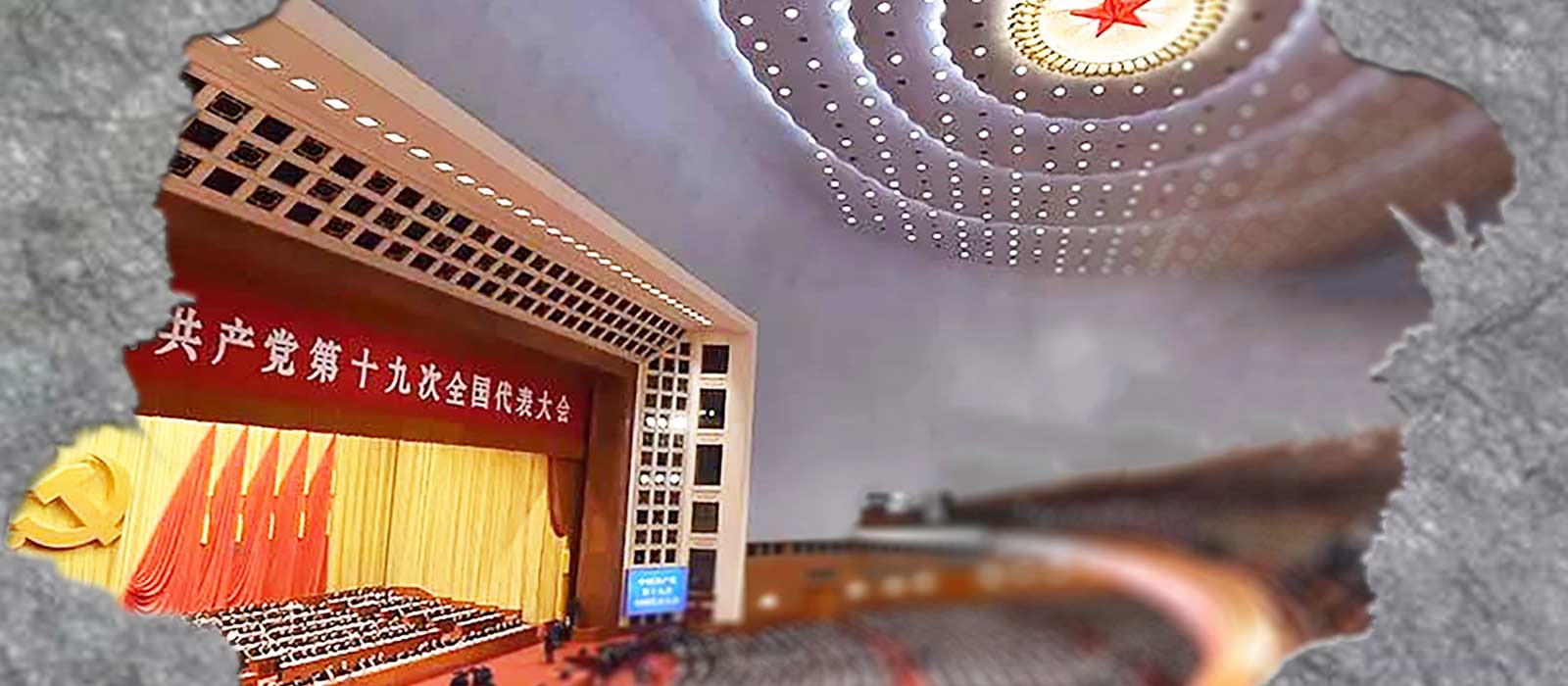「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自重也。君子必自重。《論語》中孔子四度稱讚不食周粟而殉商的伯夷、叔齊。〈微子〉篇中,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此即君子自重的最佳說明。其義有二:一、不降其志,即不看輕自己,懂得用更高的標準期許自我。因此,君子絕不會安於「小確幸」,更不會自滿於世俗名利。二、不辱其身,即重視自己的人格尊嚴,不招人輕慢。故「君子不器」(《為政》),不容許他人器使自己;「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絕不會為五斗米而折腰;甚至「無友不如己者」(見下文)。正因君子如此自重,才能贏得他人真正的尊重。所以《孟子》〈告子上〉云:「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在此指出:由掌權者或他人所恩賜的顯貴並不可靠,唯有「自重」(「貴於己者」)才是真正的顯貴(「良貴」)。
君子內在的自重,表現於外則為「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及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君子「望之儼然」,故不怒而威;但「威而不猛」,故又「即之也溫」;可是君子發言必本於良心,講求是非,態度嚴肅(即「厲」),決不故弄玄虛或不置可否,因此「聽其言也厲」、「溫而厲」;但君子之言行舉止,皆本於自身內在的自重、自信,故雖極具威嚴,但是仍然恭敬、安詳(「恭而安」)。而君子這種「安詳的威嚴」,就來自於高度的「自重」。
君子自我期許高(自重),於是不會輕易自滿,知道為學必求深思、舉一隅必以三隅反,於是能將所學盡化為己有,故「學則固」。
「主忠信」
「忠信」合稱,因為忠於自己內在的良知,才可言「信」。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諒」者「信」也,故「貞」比「信」重要;孟子亦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孟子》〈離婁下〉),故「義」比「信」、「果」重要;上二句的「貞」、「義」,都是指忠於內心的價值理念。所以孔子的「信」(對人),實立基於「忠」(對己)。故《禮記》曰:「大信不約」(〈學記〉),實有至理。我們相信一個君子,不是因為他對人言而有信,而是因為他忠於自己內心的(而且我們也信奉的)仁道。這是為什麼孔子看重「知人」、「知言」。
「無友不如己者」
〈顏淵〉篇有云:「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君子自重,故不與人品(格局、眼界)不如己者相交,以免對牛彈琴、浪費時間,或招致誤解、自取其辱。所以,此句中「不如己」之標準,不可能是財富、權勢、地位、學歷、知識、外貌,而是人品。君子自重,且「忠」先於「信」,此皆惟有其他君子可以理解、欣賞。故君子不與小人來往交遊。
「過,則勿憚改。」
君子自重而不自滿,則知有過,必改之。君子不是不犯錯,而是善於改過。《左傳》(宣公二年)晉國大臣士季言:「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後演變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即此義。
只問該不該改,不問難不難改。如冉求曰:「非不說(即「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即罵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這種劃地自限、知過不改之人,就是孔子所說的「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所以,只要「勿憚改」,就能「不貳過」,也就不算真「過」。可見孔子允許人無心犯錯,但是不允許知過不改、一犯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