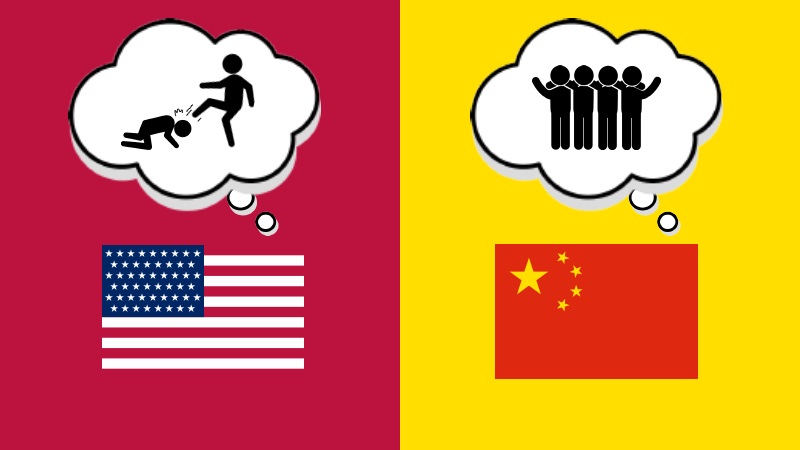無論是在大陸還是臺灣,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都是中學生語文課的必讀文章;而這兩篇於意向和風格上截然不同的散文,顯然全都體現了一定的儒家氣象,甚且是完整呈現了中國獨有而崇高的人文精神。
我們之所以如此肯定,一因這種「亭台樓閣體」的散文當為古中國所獨有;二為這般「文如其人」的自許性詩文亦罕見於古西方,更別提今日西方文壇習以「作者已死」來取消文責。
只不過,我們不免要遺憾地指出,傳統上國人習於分別閱讀兩文,而忽略了併讀尤能相較出更深厚的人文意表。如是,為能順利進行相關解讀,先附錄兩文於下: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 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 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我們以為併讀兩文而較之,實有其客觀條件上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首先,兩文皆完成於北宋慶曆六年;其次,兩人有相似的政治境遇,他們不但身處同一政治團體,還且先後因新政朋黨案被貶至地方;最後,兩位作者明顯地是在為文唱和,於互道近事之餘而各舒其志。
這種唱和實情,得由兩文分段起興之處明白見之:首先,兩文第一段起頭句都在引入全景最盛處,如〈岳陽樓記〉是「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醉翁亭記〉則為「環滁皆山也」。然後,還能將兩文二、三、四段的首句依次對照,從而看出每段前兩字出現了驚人的相似:
〈岳陽樓記〉/〈醉翁亭記〉
第二段:「若夫霪雨霏霏」/「若夫日出而林霏開」
第三段:「至若春和景明」/「至於負者歌於塗」
第四段:「嗟夫」/「已而」
我們建議從三個方向來較讀兩文。如是不妨借用〈遊龍戲鳳〉戲詞──皇帝自謂「住在那個大圈圈裡的小圈圈,小圈圈裡套著黃圈圈」,戲中像是影射大中國裡的北京城及紫禁城,於此則不妨依次借喻為「大社會的時代如北宋(大圈圈),小社會的業界如儒家(小圈圈),以及做為基礎文本的兩文(黃圈圈)」。換句話說,儘管北宋或儒家皆容有無限龐大的內含,若一旦深度掌握住兩文,當即能以為基礎而了解到:北宋為何又如何會出現這樣的文章?當時或後世儒家會如何評價兩文?再換從現代文學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只有深度掌握了文本分析,才能確定學界或業界評論的合理程度,也才能確定整個社會起了哪些作用;並從而得以理解,這兩篇文章如何能以中國特有的人文精神而昂立於世界文明之中。
壹、黃圈圈:做為研析基礎的范歐兩文本身
為能深入研析范歐兩文,我們建議借用上世紀歐陸兩大哲學流派的文本分析法:一是英伽登(Roman Ingarden)從現象學出發的文學作品解讀方案;二是巴特(R. Barthes)從結構主義引出的「S/Z」符碼分析法。
英伽登將文學作品區隔出兩個解讀範疇:「語言學結構」及「深層結構」。第一個語言學結構可以再分出兩大層級:其一是「語詞─聲音層」:〈岳陽樓記〉寫景三段常為四字一疊,較易朗朗上口而通傳人際;〈醉翁亭記〉通篇出現21次「也」字,又22次「而」字,看似拗口於文,卻又自成韻腳,實則明白串出「醉翁」喃喃之情和「獨醒」理路之清。其二是「詞句意義層」(或稱為「意義群」):〈岳陽樓記〉從洞庭湖晴雨情境大觀,進推至懷抱天下宏願;〈醉翁亭記〉則自旅途山景至賓歡主醉,盡現治政實情。
第二個深層結構亦能二分兩大層級: 一是「系統方向層」,是作者意向性的主題舖展:〈岳陽樓記〉從外界變遷到固守內心,再從民本得失到心志得償;〈醉翁亭記〉從欣遊山景到賓主盡歡,從禽鳥賓客的自知而無知,到太守有心的眾樂而獨樂。二是「圖式結構層」,是讀者意向得以揮發其成見的場合:這可以是負向的,老莊信徒或小確幸者只會覺得格格不入;也可以是正向的,或是直承孟子的獨樂眾樂之論,或是追溯《論語》裡的老問題:孔顏之樂,樂在何處?──很顯然,這「圖式結構層」已正式進入小圈圈和小社會(宋代儒家)的詮釋範疇。
巴特的文本分析法從五個符碼出發,是即文化、詮釋、行動、義素、象徵五項;但並未強制碰到詮釋對象時非得五碼並陳,而毋寧更看重讀者的解碼功力。這樣,我們且以「文化」符碼為例,它直涉大、小社會語境,既有助於確定文本本意,亦能回饋增益社會語境的解讀樂趣。比方一旦得知范仲淹實未去過岳陽樓,或即能倏然領悟:何以〈岳陽樓記〉的洞庭湖景可複製於一切大湖?又何以其四言寫景特易讓人了悟、熟悉而善誦?這裡涉及我個人的一次解讀經驗:我在上世紀曾遊三峽,特於城陵磯下船搭車轉赴岳陽,目的就是要看岳陽樓。孰料登樓一望卻是大吃一驚,因為〈岳陽樓記〉起頭所謂的「銜遠山,吞長江」並不存在,眼前只有一個矮小的君山島,而長江距此還有15公里!然而,這趟經驗卻讓我感悟到:原來該文中的洞庭湖景實能見諸所有大湖。而後領會〈醉翁亭記〉也有完全不同的如實寫景過程,從而逐步推引出比較兩文的可行性。1 再比方本文一開始提到中國獨有的人文精神時, 所論及的若干理由亦皆得屬於文化符碼。
然後來看「義素」符碼。它本來專指意義的最基本元素,巴特則以之為人物性格──畢竟影響事件進展的關鍵,常在乎參與者的性格特質,且常是這種特質最能逗引讀者的關注。惟須注意:個人性格或還能發展乃至昇華為某種人格。這樣,於〈岳陽樓記〉中,原來范仲淹傳記所示的嚴謹性格,得升至卓然不群的偉岸人格;再於〈醉翁亭記〉中,相傳歐陽修的寬和性格,得躍為人格上的達正:因為達觀,所以能於山水自然與人際交誼上得享如此歡樂;因為周正,所以能在醉醒之間調適得如此堂正而周到。
最後來看「象徵」符碼(或譯「徵象」符碼),巴特建議將之視為一系列二元對應的類聚關係對比,而我們當即能見出「〈岳陽樓記〉/〈醉翁亭記〉」這樣一組看似信手拈來的象徵符碼,其實可以推演出一張結構樹狀圖如下:

限於篇幅,我們在此不多作詮釋推衍,唯且以右下最後一組為例。做為最高格調的壯志「樂觀未來/樂起當下」,實則范仲淹樂觀未來之時,未必無視於當下治績,而其文中先述滕子京「政通人和」, 實如稱述自己的暗喻修辭;至於歐陽修之樂觀當下,實是於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之樂的當下,更期以太守之醒能兢業自守而終致進施治政大業。
貳、小圈圈:宋儒會如何評論兩文
我們讀北宋歷史可以推知,約莫就是在〈岳陽樓記〉發表那年前後,曾發生兩件有趣事件:一是歐陽修初見青年王安石,鼓勵其用功得成就如韓愈,而安石卻答以:「實願成如孟子」;二是少年兄弟程顥、程頤首訪周敦頤,臨別時後者鼓勵兩人回去當深思:「孔、顏之樂,樂在何處?」看來很顯然,就像漢唐讀書舊習那樣,《孟子》和《論語》仍為北宋士人熟讀對象;從而很自然,我們得由這兩部書出發,以檢視宋初士人界小社會對兩文的解讀傾向和評價依據。
針對兩文基點「何時而樂」與「眾樂獨樂」,再配合上提兩樁事件,我們先擷取《孟》、《論》幾段引文,以為論述小社會的評價依據。
1、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王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孟子曰:「今王鼓樂於此,⋯⋯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ㄨㄤヽ)矣。」《孟子.梁惠王第八章》
2、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ㄨㄤヽ)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第十一章》
3、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第七》
4、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點,爾何如?」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先進第十一》
5、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第十二》
我們先來看《孟子》的兩段引文。第一段先要確悉君王亦肯定獨樂不如眾樂,然後即強調君王施政若傷民則難有眾樂,唯利民始能享眾樂。換句話說,不是君王想要眾樂就能眾樂,而是端賴能否行仁政於前。顯然,這裡是借獨樂不如眾樂之說, 以助成君王行仁政而後樂的儒家之道,亦即從仁政到眾樂有個時間差。於是如果輔佐君主的條件不變,范歐兩人皆樂有仁政之後的眾樂──唯此時即碰到空間差的問題,而這就來到第二段引文。
在後者中,孟子直言「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肯定仁政施行須以天下格局為準; 於是可以看到,當范仲淹自問「何時而樂?」再自答「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時,他顯然更近於孟子之言。然而,一則全天下皆行王道的時間遙不可期,二則決定權操於君王而更遠不可待, 從而范仲淹的「樂以天下」實屬儒士們的千古悲情。或即因此〈岳陽樓記〉得為千古至文,且名聲常大於〈醉翁亭記〉。
相形之下,歐陽修的正當性則有賴第四段的《論語》引文。其中可以看到,處理好小城或宗廟之事,亦能算是邦國大事。於是,歐陽修無待於天下大治,只要滁州得治即可;無恃於君王遙控,只需太守親持即可;於是在〈醉翁亭記〉中,我們看到歐陽修小小善治之後的即時行樂,而且是得享眾樂之餘的獨樂。
換句話說,同樣都持有「眾樂vs. 獨樂」的念頭,范仲淹執著於君王天下的時空距離,像是自匿於悲劇英雄的恆常之「憂」;歐陽修則自足於太守治州的小小格局,也就成就了討喜角色的即時行「樂」。
我們接著來看《論語》的三段引文。第三段猶如起了個頭,也就是周敦頤就此提醒程氏兄弟的「孔顏之樂,樂在何處?」第四段孔子之言「吾與點也」的暮春之遊,嘗由宋儒讚為「道家氣象」,像是稱頌其行樂境界,亦即對周敦頤的問題做出了解答。如此這般的春遊即景與享樂隨意,豈非正合乎〈醉翁亭記〉裡的敘事語境?然而一旦聯繫起該引文後續的為政之言,卻更吻合了中國傳統士人為官則儒、休致則道的生活態度。
只不過「吾與點也」畢竟是孔子喟嘆之言,是他一時的感慨,而非他平素汲求之行。事實上,如果我們了解到《論語》編輯理路,知道其篇章聯繫的巧思性,當即能看到第四、五段分別為〈先進第十一〉末章與〈顏淵第十二〉首章。換句話說,前篇末章才稍作春遊之嘆,隔篇首章即正言歸仁四目的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後者是最嚴格的剛毅自制,是做為「天下歸仁」的前置修養,使范仲淹坦然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安身立命之道。
換句話說,范仲淹面對著「天下歸仁」的遙遙無期,仍能自持於「後天下之樂」的安身立命之道,這或許才是〈岳陽樓記〉使儒生歸心的主要原因。
參、大圈圈:北宋社會何以會產生兩文這樣的作品?
我們現在來到文學社會學的大社會範疇,也就是既要探索何以北宋會出現這樣的作品,還要了解何以這樣的人文精神會傲然於西方世界,且特別是對於整個文藝復興時代。
我們首先來看范歐兩人所處的北宋有何特質。
當然,我們絕不能輕忽周代以來兩千餘年的文化傳承:它先是周公取消殷人尚鬼政治而改奉「敬天保民」國策,且此後習為領有龐大疆域的君主封建政體;再是孔子建構起來的儒家士階層,他們於國家是依歷史經驗而行民本之治,於己身則踐行《論語.子罕篇》首章的「子罕言利, 與命,與仁」(儒者極少談個人利益,而是更多地履行立命行仁之道)。從而很顯然,范歐儒者本即有可能寫出〈岳〉、〈醉〉這樣的至文。
然而,如果反問何以在宋以前看不到這樣的至文,則可以北宋的時代特質現身說法。首先,北宋恰是中國第一個進入平民社會的朝代,而其歷史性原因有二:一是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使平民有機會大舉翻身,二是三國兩晉以來長期世襲的士族政治已結束於唐末。如是即出現第一個關鍵點:范歐兩人皆為平民出身,自易貼近平民苦樂。
其次,儘管北宋人有完整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基本上不採宗教信仰的宋儒,卻能一方面圓融地化掉了佛教和道家的中心義理,二方面依舊奉行修齊治平的倫理規範。如是,宋儒更易展現「民胞物與」的寬宏胸懷。
再次,北宋尤其是中期以前的大詞人皆為國之重臣,詞中深情如范仲淹的「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或歐陽修的「庭院深深深幾許,⋯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這樣的詞風與歷練自有助於寫出文情並茂和情景交融的〈岳〉、〈醉〉兩文。
又次,宋太祖於立國之初即宣稱要「以文化成天下 」,而採「佑士」政策:一則明令「不欲以言罪人」,繼則改用文臣充當武將,三則由皇帝親定殿試名次, 從此進士皆為天子門生,且一中進士即授官,不需再經吏部選試。這是《論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理想實踐。正是在此儒家君臣大義氛圍中,范仲淹遭貶仍於〈岳陽樓記〉說「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歐陽修被貶,則在藉〈醉翁亭記〉抒己治績樂事之餘,終亦於同年的〈豐樂亭記〉稱頌地方長年安定全賴皇恩浩蕩。
最後,正是上述多重因素的組合,宋儒更能堅持《論語》所謂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於是他們一則堅守其道德修養,范仲淹一生清心做官, 清廉自守,歐陽修自詡為「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二則關注王道理想及現實問題,還將之落實到具體行動: 既有范仲淹、歐陽修等鼓吹慶曆新政, 又有士大夫的上諫成風,乃至於貶官仍能持志續求善治;三則必能不耿耿於得失、不汲汲於目前,而要展現其為政濟世的人生藝術於人品文章之中──這就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以及歐陽修的〈醉翁亭記〉。
肆、圈外:為何西方人文主義者寫不出這樣的作品?
我們接下來看: 何以〈岳〉、〈醉〉兩文不會出現在文藝復興時代?我們之所以要做此比較,原因首在現代史學界已習於稱北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與之相比更顯師出有名;其次則因西方歷史過長,自難照顧周全,而四百年的文藝復興恰恰在西方文明中承先啟後,因而最具代表性。
但再進一步分析前,有必要先突出文藝復興與北宋的基本差異。首先就是時間差:西方文藝復興從14到17世紀,橫跨400年;北宋從西元960年至1127年則只有167年,只占西方文藝復興不到一半的時間。
這樣的時間差呈現出兩個現象:一是北宋的結束幾乎要比文藝復興的開始還更早300年,而兩者之間的銜接者則為蒙古帝國,其中關鍵在三次西征將北宋的火藥、羅盤、造紙術和印刷術等科技傳到西方,影響到文藝復興時期幾個重大進程。
第二個時間差現象在於內含重大進程的數量差異:北宋在徽宗以前可說安定地處於儒家主導之下,只在經學上出現理學,在政治上發生變法。文藝復興400年則先是出現人文主義運動,16世紀開始宗教革命、海外擴張與科學發展,17世紀中出現了現代主權國家。
進而言之,首先是14、15世紀的人文主義運動,這兩世紀大部分仍重疊著中世紀後期,知識界開始重尋古希臘的人文著作,但鄙視世俗財富幸福的天主教仍據主導地位。事實上,當時著名的人文主義作家仍以宣教作品為主,而這也可能涉及令人無助而只能求告上帝的天災:黑死病侵襲歐洲一百多年,而1451年甚至害死了1/3的歐洲人口。
其次是16世紀開始的宗教革命與殖民主義。1517年路德(M. Luther)貼示《九十五條論綱》,批判羅馬公教的腐敗及傳道的專橫,從而要求改革教會傳統,導致新教革命及未來百餘年的宗教戰爭。我們須注意:人文主義運動只觸及一小群文化人士,而宗教改革則涉及到所有上、下層人口。至於殖民主義,是由葡、西開始,其後歐洲國家紛紛加入並持續了好幾百年,同時並因航海和軍事科技引發了即將來到的科技革命。
最後是17世紀中出現了現代主權國家,亦即於30年戰爭後,歐洲諸邦於1648年締結《西伐利亞合約》,確認了主權的原則,誕生了現代國家。它們仍然繼續著歐陸與海外的爭霸戰爭:戰爭需要集權,長期戰爭需要專制,於是新生現代國家多行君主專制政體,以建立常備軍,連帶需要配有財政力量、司法秩序及奉行中央號令的公務團隊。
在整個歷時400年的文藝復興時期裡,我們首先看到回望希臘而相當薄弱的人文主義運動,其整個人文精神的重現力量遠不如宋儒。然後,16世紀開始的宗教革命與儒家民胞物與的志氣距離很遠,野蠻的海外殖民帝國主義完全無涉國家善治;航海引發的科技發展還要到 18世紀才能帶出工業革命。最後,17世紀中出現了現代國家,其備戰為主的君主政體更是遠離了民本為重的北宋。很顯然,范、歐兩人的鴻文絕不可能出現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而其中道理多少已被韋柏(M. Weber)聞到一些端倪:
「中國的官大人在出身上,和我們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學者相似,⋯⋯中國這個階層挾其取法中國古代而發展出來的規矩,決定了中國的整個命運。如果當時的人文主義學者也曾稍有機會取得同樣的影響力,我們的命運也許是一樣。」(韋伯,〈學術做為一種志業〉)
因此,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終究只能出現於北宋時期的中國,而不可能出現於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