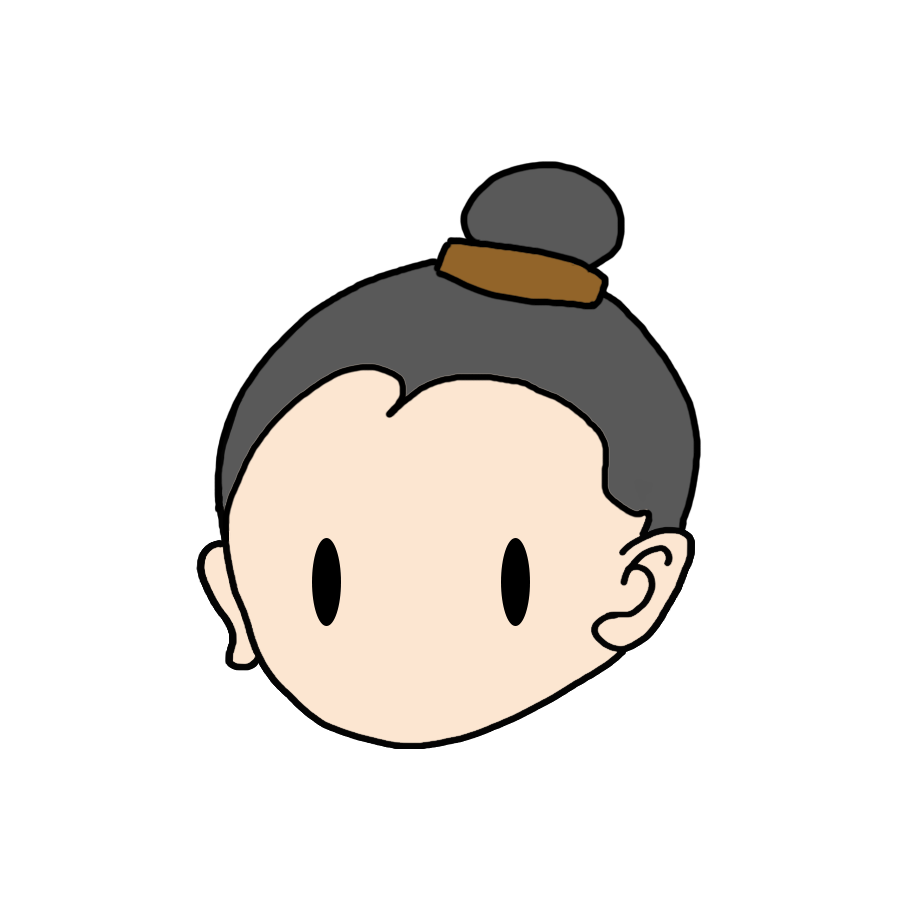
一位朋友曾說:於一名運動者而言"Anger is important." 確實,憤怒(即:對現狀的不平之氣)是非常重要的,但事實上,Anger is only a trigger,憤怒只是一名運動者誕生的催化劑。關鍵在於,憤怒究竟能不能推動一個人去思考:「我與運動的關係是什麼?」尤須指出的是,這是一個「關係本位」的問題,而不是一個「以我為本位」的問題。換句話說,問句的主詞是「我與運動」這組關係,而不是「我」這個個體。以「我與運動」為主詞,那要不要參加運動,就是個涉及我是誰,運動的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我如何貢獻己力推進運動的問題。這個問題作為一種道德選擇,其要求思考者具備是非觀、現實感與責任心。以「我」為主詞,則是否參加運動,就成了一個非常私人,無關大我,甚至非常功利的問題。舉例言之,按理講,島內政治大潮既然是仇共反中,基於台灣社會如當今世上絕大多數社會那樣對男性有較多的期待,男性被認為應該肩負更多的家庭責任與社會責任,可以想見,統運的參與者必然是以女性為主,而不是男性。然而,現在在大陸活躍的台青,男多女多?顯然是男性更多了。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他們之所以「參與運動」(實際上是高舉紅旗、自我標榜),是因為他們決定參與其中的「決定」本身,發源於「以我為本位」的問題,即:「我」參與「運動」能獲得什麼?儘管他們中絕大多數確實看出商機,找到門道,在「參與運動」中把權、錢、名都給掙了,但基於問錯問題,他們注定不能是真正的運動者,也注定只能是逐利的,而不是大公小私,以公為先的。大公無私更是不可能。
說回到朋友所提的"Anger"。憤怒究竟重要,但它只是提出正確問題,並推動一個人以正確方式思考問題、得出答案,成為合格運動者的動力。換言之,憤怒只是一名合格運動者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一旦「以我為本」,問題提得不對,思考方式偏差,縱有再強烈的憤怒也無法讓此人轉變為合格的運動者。這樣徒有憤怒的人,只能是給運動添亂的盲動者,或者「嘴上都是主義,心裡都是生意」的利益派。更何況,憤怒作為一種情緒,必然隨著時間流逝、問題問錯、思考偏差而逐漸消散。當一個人開始逐利,把中國統一當成談資,把每一次露面、上台、握手、合影純當資本積累,還論的上什麼憤怒?對台灣社會的現狀能有什麼不平?
根據上述邏輯,我們可以斷言:島內絕大多數所謂的統左,他們的意識形態是假的。馬列毛的思想做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是以「解決問題」為目標,而「解決問題」的前提是「理解客觀現狀」與「確定應然目標」。此所以「解決問題」即「路線規劃」,即連通「客觀現狀」與「應然目標」的工作。由此可知,島內多數統左既是「以我為本位」地思考統運,那麼他們對運動的由來與發展,必然是基於「自己」的想像或利益,而不是基於客觀事實(即:真實存在的島內認同矛盾)。畢竟對他們來講:怎麼樣「幻想」統運於「我」有利,怎麼想便是。至於「解決問題」與「路線規劃」,與(物質利益或精神高潮的)自我滿足相比,有何重要的呢?於是,島內統左圈子有個怪象,即從1950年代至今真正的運動者少之又少,多的是幻想家和利益派。
假如幻想家、利益派與運動者之間的差異,涉及根本性的「義利之辨」,關乎長時間對價值選擇與自我定位的思考,那我們豈能癡信幻想家與利益派能輕易發生轉變?統一大業與統後和平又豈能交託於幻想家與利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