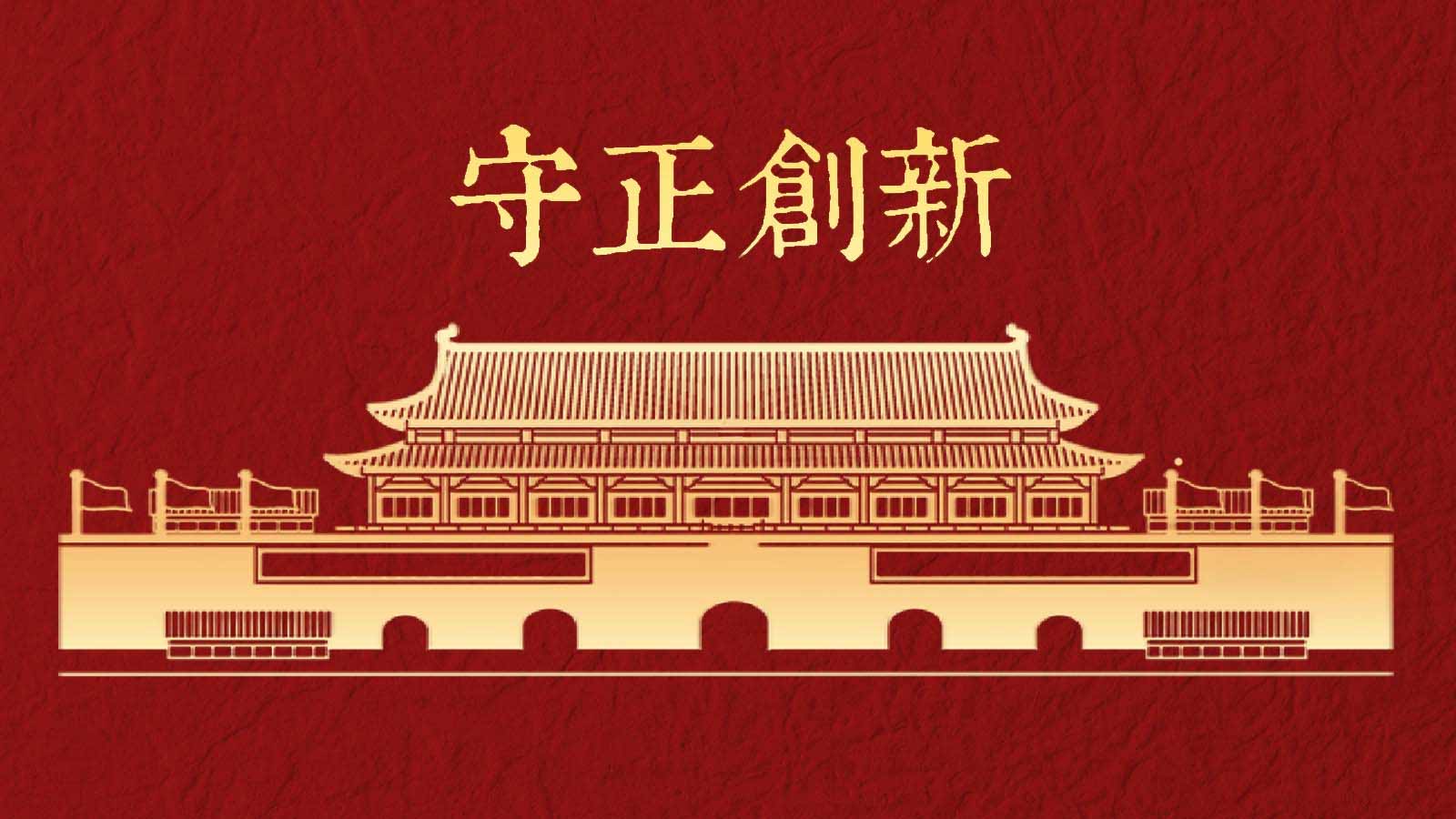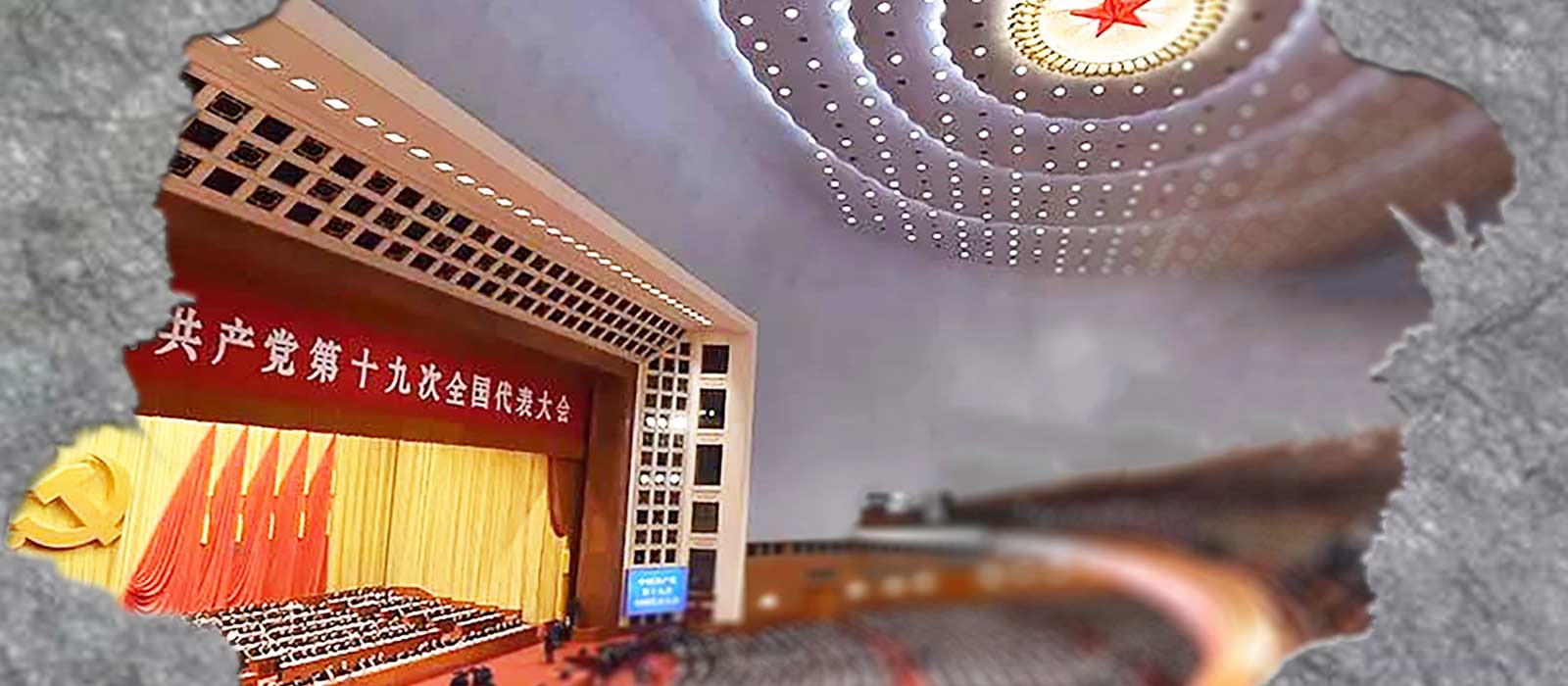在完成《論守正創新作為新時代黨的思想路線》和《論中國知識界的守正創新》之後,如何將守正創新應用於中國法學界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我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2020年11月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如何全面準確理解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擺在中國法學界面前的重大課題。
新中國法學的進步
事實上,16年前,中國法學界曾經轟轟烈烈地討論過守正創新問題。2005年,鄧正來教授發表長篇論文《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該文2005年分四期首發於《政法論壇》,2006年由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2011年再版。本文所引用的是《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第二版),商務印書館,2011年。後文簡稱「鄧文」。2 ,通過對26年來(1978年-2004年)中國法學的四種範式——「權利本位論」、「法條主義」、「法律文化論」和「本土資源論」——進行批判,論證中國法學界接受了一幅「移植」進來的、未經審查或批判的、以西方現代性和現代化理論為依託的「西方法律理想圖景」作為法治中國的目標,未能深入探究「中國人究竟應當生活在何種性質的社會秩序之中」,自然也就缺乏「中國法律理想圖景」。鄧正來宣示「我們必須結束這個受『現代化範式』支配的法學舊時代,並開啟一個自覺研究『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法學新時代。」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第二版),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3。3 鄧文後來以「鄧正來問題」引發了廣泛討論,這些討論不管是贊同鄧正來所主張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還是仍然堅持「西方法律理想圖景」是唯一普世圖景,無疑都使得問題的討論更加深入。專門評論該論著的論文集有兩部:《分析與批判:學術傳承的方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檢視「鄧正來問題」:《中國法學向何處去》評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4 鄧文更大的貢獻在於,其從對中國法學的批判入手,引出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在全球化時代,如何將「理想圖景」引入對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的思考——這在根本上意味著,中國不僅要成為一個「主權性中國」(China with sovereignty),更要成為「主體性中國」(China with subjectivity)。世界結構中「中國」的實質不在於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個性,而在於主體性,尤其在於思想上的主體性——其核心在於形成一種根據中國的中國觀和世界觀,並根據這種中國觀和世界觀以一種主動的姿態參與世界結構的重構進程。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第二版),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2-3。5 可以說,「鄧正來問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後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回答,那就是2020年11月提出的習近平法治思想。
從改革開放之初「幼稚的法學」到2004年「西化的法學」再到守正創新的「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國法學在不斷進步。改革開放是一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優秀成果的過程,法治毫無疑問是其中之一,對於剛剛從十年動亂中走出來的中國人民來說,不管是學哪種法治,總是優於人治的。鄧正來所批判的改革開放之後的四個法學範式,代表了中國法學界學習西方法治的不同認識範式。16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從四個範式的進一步發展看到中國法學的進步。
鄧正來第一個批判的是張文顯的「權利本位論」,也是批判得最有力的。張文顯的「權利本位論」立場鮮明地代表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其基本觀點是:個人的權利和義務是法哲學的中心範疇;權利和義務的地位有主要與次要、主導與非主導之分;古代法是以義務為本位,現代法則是或應當是以權利為本位。張文顯,《法哲學範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42。6 張文顯鮮明地支持「權利本位論」:「筆者把權利確定為現代法哲學的基石範疇。權利作為現代法哲學之基石範疇的理論表達是『權利本位論』,所以,也可以說,『權利本位』是現代法哲學的理論基石。」張文顯,《法哲學範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35。7 鄧正來深刻地揭示出,張文顯的「權利本位論」實際上是一種不同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新「政治–法學」。張文顯提出權利本位論的初衷在於改革開放後的政治變革:「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否定了持續二十多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同時,全會著重提出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麼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法學理論,那就與實踐背道而馳;要麼徹底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法學理論,重新建構一個與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實踐和社會發展方向相適應的法學理論體系。」張文顯、姚建宗、黃文藝、周永勝,〈中國法理學二十年〉。轉引自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第二版),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68-69。8 鄧正來認為,「權利本位論」主要是在與「階級鬥爭範式」的論爭中逐漸形成的。張文顯、姚建宗、黃文藝、周永勝,〈中國法理學二十年〉。轉引自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第二版),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69。9 事實上,張文顯的「權利本位論」並不是什麼創新,只是將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的理念表達了出來。對西方法哲學有深入研究的香港大學法學院陳弘毅教授明確指出:「『權利本位論』對權利這個概念作為法的基本或『基石』範疇的理解,源自西方近現代法學傳統而非中國法的傳統。但是,必須指出,『權利本位論』在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的形成和發展,有其十分獨特的中國語境。在當代的西方世界,『權利本位論』成為顯學是難以想像的,因為在當代西方的語境裡,根本不會有需要提倡權利本位,它基本上已是天經地義、不證自明的東西。」陳弘毅,《中國法學往何處去》,收錄於《檢視「鄧正來問題」:《中國法學向何處去》評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10 只要選擇法治道路,權利保障是必然要求,然而權利保障並非必然意味著要以基於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權利為本位,正如自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之一,但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必然堅持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張恒山教授明確提出「義務重心論」:就法律的構成而言,義務性規則是法律的主體;就法律的適用而言,義務性規則的存在是追究個體責任的前提;就法律的發展史而言,先有義務性規則,後有授權性規則;就法律的價值而言,義務性規則是保障社會基本秩序和支撐個體自由所賴以存在和展開的框架;就義務和權利的關係而言,義務性規則的確定和對義務的信守是權利界定和權利獲得的依據。張恒山,《義務先定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11 相比之下,張恒山的「義務重心論」更為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法治事實。令人遺憾的是,「權利本位論」者將「義務重心論」塑造成「義務本位論」,並將之稱為體現封建色彩的法律觀念。張恒山,《義務先定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後記。12 鄧正來深刻指出,「『權利本位論』與『階級鬥爭範式』的論爭雖說主要是一場法理層面的論戰,但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講,它卻是在一種彼此雙方都承認的更高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展開的論戰。因此,論爭的雙方不僅都宣稱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般的方法論和最高的認識原則,而且他們也往往都把他們共同認定的經典論著中的觀點或者他們對這些觀點的解釋作為一種『最終正確』的判準加以訴諸。」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第二版),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73。13 在「階級鬥爭範式」、「義務重心論」與「權利本位論」的論爭中,張文顯的「權利本位論」取得了暫時的勝利,原因可能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很多法律人心目中就是資本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前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儘管在經濟上還落後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政治上毫無疑問比資本主義優越。從「以階級鬥爭為綱」時代走出來的人,強調權利保障,甚至於有點自由主義傾向是可以理解的,這是「權利本位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我們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權利本位論」,實際上,「權利本位論」只是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巧妙表述而已。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到新時代,在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其他什麼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和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定位下,「權利本位論」需要重新被審視。鄧正來將張文顯的「權利本位論」定位為「政治–法學」是非常敏銳的,政治方向發生了變化,「政治–法學」範式隨之就要發生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2020年11月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標誌著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和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新起點,代表了「中國法律理想圖景」努力的方向。當前張文顯是習近平法治思想最積極的宣傳者。張文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體系》,載於《法制與社會發展》2021年第1期。在該文中,張文顯高度讚揚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內涵豐富、論述深刻、邏輯嚴密、系統完備,在概念上系統集成、在話語上自成體系、在邏輯上有機銜接,展現出鮮明的理論風格、深厚的歷史底蘊、開放的全球思維和雄渾的實踐偉力,蘊含著睿智的法律哲理、鮮活的法治道理、深刻的法學原理、雋永的法律情懷。」14 從張文顯近幾年所發表的論文來看,他試圖調和權利本位論和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張文顯在對民法典的評論中明確堅持「權利本位論」:「法律的真諦在於確認和保障權利。民法典的根本法理就是以人民為中心,其核心要義是以權利為本位。我國民法典構建了以人民為中心、以權利為本位的完整的權利體系。」張文顯,《民法典的中國故事與中國法理》,載於《法制與社會發展》2020年第5期。15 張文顯援引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作為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法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依法維護人民權益、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重大意義。」中共中央政治局於2020年5月29日下午就「切實實施民法典」舉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轉引自新華網。 16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依法維護人民權益」所要維護的是作為群體的人民的權利,是集體主義的權利保障,可以理解「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權利為本位」,與張文顯的「以權利為本位」的差距比較大。退一步講,即使我們承認民法典是以權利為本位,是否就意味著所有社會主義法律都應該以權利為本位呢?張文顯在總結中國法學的成就時仍然堅持整體的「權利本位論」。他明確指出,「中國法學70年的探索歷程,也是批判舊範式、形成新範式的範式更替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學界深刻反思、全面批判、果斷拋棄業已嚴重阻礙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的『階級鬥爭範式』,在立足實踐、綜合分析、系統論證的基礎上,形成了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人權保障相適應的『權利本位範式』。」張文顯,《中國法學現代化的理論宣言》,載於《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0期。17 「階級鬥爭範式」確實阻礙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但是否意味著社會主義法治就是張文顯基於西方資本主義法治提出的「(個人)權利本位範式」呢?我們可以寬泛地理解「權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許決定了經濟行為應該以權利為本位,但說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和人權保障也是以(個人)權利為本位,可能違背大多數中國人自古以來習以為常的觀念。更值得質疑的是張文顯認為「從『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從法律體系到法治體系、從義務本位到權利本位的飛躍。」張文顯,《中國法治40年:歷程、軌跡和經驗》,載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年第5期。18 我們都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在十八大前提出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來的,「良法善治」也是十八大後提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最大的區別是「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如果說適用於公民的國家法律是以權利為本位還可以理解,那麼黨內法規應該以權利為本位則根本違背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原則,因為《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黨員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顯然是以義務為本位。《中國共產黨章程》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公民權利排在公民義務前面,而是將黨員義務排在黨員權利前面,也可以說明黨員應該以義務為本位。張文顯的法治觀念的根本問題在於,沒有區分社會主義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現代性,沒有區分社會主義法治與資本主義法治。在張文顯看來,法律只有古代與現代之分,古代法是以義務為本位,現代法是以權利為本位。近兩年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外治理效果表明,以個體權利為本位的治理模式失敗了,而以人民權利為本位的治理模式獲得極大成功。在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公民來說,以權利為本位還馬馬虎虎說得過去,但對於共產黨員來說,義務和責任應該是首位的,以權利為本位是萬萬不可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法治到底應該「以(群體的)人民權利為本位」還是「以(個人的)權利為本位」或者「義務重心論」?這是一個無論是對於法律實踐還是建構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都是至關重要的方向性問題,中國法學界有必要重新進行一次大討論。不管張文顯是完全信仰習近平法治思想還是試圖調和「權利本位論」與社會主義法治,張文顯的「政治–法學」確實與時俱進地發生了重大轉折。我們可以斷定張文顯的「政治–法學」 已經取得了某種進步,這是中國法學進步的標誌,但是仍未根本解決法治中國的法理基礎問題。
鄧正來對法條主義的批判是最弱的,也未能給出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觀點。鄧正來對朱蘇力的批判有些牽強附會,因為朱蘇力並沒有接受「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而是劉大生所說的追求「本土法治」劉大生,《從「本土資源」到「本土法治」——蘇力本土資源理論之學術解構》,載於《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19 。鄧正來批判梁治平時,梁治平已經從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法律文化論」範式邁向同情理解不同法律文化類型的「法律的文化解釋」範式了。更難能可貴的是,梁治平根據治理方式的不同將中國文明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基於十八屆四中全會取得的成果,梁治平認為第三波文明初露端倪。梁治平,《論法治與德治——對當代中國法治運動的一個內在觀察》,原載《中國文化》2015年第1期。收錄在梁治平,《論法治與德治——對中國法律現代化運動的內在觀察》,九州出版社,2020年。20
鄧正來對四種範式的選擇是自由舉例式的,可能是根據這些範式的影響力,而不是基於不同類型法理學範式,所以不是窮盡式的批判。並且鄧文是批判式的而非建構式的,並沒有正面回答「中國法學向何處去」的問題,而是僅僅回答了「中國法學不能往何處去」。鄧正來認為,中國法學不能受西方現代性的「西方法律理想圖景」支配,但對西方現代性到底是什麼?我們為什麼不能接受西方現代性?鄧文沒有給出回答。鄧文在批判之後也沒有給出「中國法律理想圖景」,而是以一句狡猾的「當我把你從狼口裡拯救出來以後,請別逼著我把你又送到虎口裡去」,將必須正面回答的標題「中國法學往何處去」拋到了九霄雲外,此說法可能受伏爾泰的影響。伏爾泰當年僅僅抨擊了基督教,而沒有提出一個替代,他對此的回答是「我從兇殘的野獸口中救了你們,而你們卻問我以什麼替換這個野獸!」伏爾泰的啟蒙哲學是革命哲學而非建構哲學,只知道基督教吃人,必須拋棄。鄧正來也只知道中國法學不能一味接受西方現代性的「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而應該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但他並不知道「中國法律理想圖景」到底是什麼。所以,鄧文的標題《中國法學往何處去》應該改為《中國法學不能往何處去》。當然,我們不能苛求思想家,一些思想家只會革命,另一些思想家只會建構,既能革命又能建構的思想家是百年難遇的。中國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知識界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鄧正來敏銳意識到了中國法學界和中國知識界將發生的變革,他知道不能走過去的老路,只是進行知識引進,中國知識界應該進行知識創造。知識創造或許不是鄧正來這一代學者所要完成的使命。鄧正來後來的著作《誰之全球化?何種法哲學?》(商務印書館,2009年)雖然進一步強化了「以中國為根據的分析框架」,但也沒有知識創新。21 如何從學理上進一步建構和體系化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時代中國法學界的使命。
守新中國之正
鄧正來的批判僅僅集中在改革開放後的26年,且僅僅停留在對四個法學範式的批判,這對於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建構新時代法學應該有大歷史視野,從大歷史來分析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建構新時代法學不僅僅需要對「中國法律理想圖景」和「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背後的政治進行剖析,還應該基於習近平法治思想進一步思考「人類法律理想圖景」,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和未來出發才能看清楚「西方法律理想圖景」和「中國法律理想圖景」。
自鴉片戰爭始,中華民族就開啟了學習西方的過程,不同思想派別之間的區別在於如何學,從「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到「中體西用」(張之洞)、「全盤西化」(胡適)、「西體中用」(李澤厚)和「中體全用」(柯華慶)柯華慶,《第三次變革》,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22 的觀點都有。通常認為,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學習西方經歷過三個階段:器用學習階段(洋務運動)、制度學習階段(百日維新)和文化學習階段(新文化運動)。在一定意義上講,改革開放是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權已經穩固條件下重新開啟的全面學習西方的現實選擇。改革開放之後,李澤厚的「西體中用」代表了學習西方的思潮,李澤厚認識到鴉片戰爭之後學習西方的過程被「救亡壓倒啟蒙」所中斷,改革開放應該重啟啟蒙,因此提出「啟蒙主體性理論」。李澤厚的「啟蒙主體性理論」所借助的思想資源是源自西方的,是追隨康德並戴著康德有色眼鏡來看待問題的,其「啟蒙主體性」實質上是「主體性的人」,「主體性的人」烙上了以康德為代表的西方啟蒙思想的抽象人性論色彩。呂勇,〈當代中國思想界對主體性的兩種討論——以李澤厚「主體性的人」與鄧正來「主體性的中國」為例〉,收錄於《檢視「鄧正來問題」:《中國法學向何處去》評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23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西之爭」是理解中國問題的基本框架,並且「中西之爭」逐漸演變為「古今之爭」和「劣優之爭」:中國的今天是西方的昨天,中國的明天是西方的今天,中國的未來是由西方所設定的。 呂勇,〈當代中國思想界對主體性的兩種討論——以李澤厚「主體性的人」與鄧正來「主體性的中國」為例〉,收錄於《檢視「鄧正來問題」:《中國法學向何處去》評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24
古今中外之爭從根本上說是哪個主體將引領世界之爭。學者們常常在中學與西學之間的糾纏,忘記了主體不是學,而是人,中學是中國人發展出來的文明,西學是西方人發展出來的文明,中學和西學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發展的,學習是主體在學習,學習是為了趕上和超越。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是天經地義的,不會失去主體性,因為科學和技術沒有中西或國別之分。文化學習是綜合的,是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的問題。1915年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主張做「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新青年,但無論怎麼強調學習的重要性,每個人都不可能成為其他人,每個國家也不可能成為其他的國家,因為每個人的基因不同,每個國家的歷史不同。
在制度學習中是否要進行法律移植,也基於同樣道理。制度類似於衣服,正像衣服能夠禦寒避暑和美化形象,最合身的衣服都是量身定做的,每一個好制度都是最適合主體進步的。因為人與人體型身高的相近性,根據標準身材量身定做的衣服可以批量生產,人們到商場購買衣服比到裁縫店量身定做成本低得多。法律的移植就像到商場買衣服,如果一個人能夠買到剛好合身的衣服,說明曾經量身定做的人的身材、體型和審美與之相同或者相近;如果大體合身,讓裁縫稍微改一改就可以穿;如果一個人的身材體型比較特別,例如太高或者太胖,那麼在商場就難以買到合身的衣服,只能量身定做。人與衣服的關係應該是衣服符合於人而非人去符合衣服,一個高個子買了一件短衣服所以就將自身變短是可笑的。然而,中國法律人常常在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移植問題上犯這類可笑的錯誤而不自知。
明確了主體與法律移植的關係,中國法學界就可以做到根據中國追求的價值和國情有選擇性地移植、修改和創造法律制度,實現「中體全用」,這個「中體」不是中學或中國文化,而是中國主體,不是舊中國,而是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要全盤復興中國古代文化,而是要復興與曾經在天下秩序中的中心大國地位類似的全球領導地位。當然,新中國不是以腦袋空洞的一群生物學上的「中國人」為主體,也不僅僅是以偶爾居住在一塊不知為何叫做「中國」的地區的一群人為主體。 作為「主體」的「中國人」是有文化傳承的。因此,「中體」不能只是指一群人,而應該包含某些中國特有的核心價值。在近代以前,這種核心價值就是儒家的「性善論」及「民本」;在近現代,則是「社會主義」及「共同自由」。中國人民之所以接受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是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密切相關的。
現代性包括資本主義現代性和社會主義現代性。鄧文的核心概念是「現代性」、「西方」和「中國」,但文中的「現代性」和「西方」都是唯一的,「中國」也沒有新舊之分。現代性打破了「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觀念,打破了「人生來都是臣民」的觀念,「人生來是自由的」觀念得到廣泛的傳播和接受。盧梭,《社會契約論》,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4。25 人人自由和平等是現代性最重要的成果,是一切現代制度建立的基礎。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現代性」就是唯一的。事實上,法國大革命後有兩條路線,一種是平等主義者的主張,另一種是利己主義者的主張。革命勝利後,利己主義者占據優勢,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通過代議制為資本主義蓋章。代議制事實上不是民主制,而是貴族制,只不過不是封建社會固定的等級貴族制,而是自由流動的以資本多少為判斷標準的自由貴族制。
施特勞斯將現代性分為三波:第一波現代性、第二波現代性和第三波現代性。其第三波現代性實際上是後現代性。凱瑟琳•紮科特、邁克爾•紮科特,第二章〈施特勞斯—現代性—美國〉,《施特勞斯的真相:政治哲學與美國民主》,宋菲菲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26 除去後現代性,西方現代性分為兩波:第一波現代性和第二波現代性。由馬基維利(Machiavelli)開始,包括霍布斯、斯賓諾莎、洛克等人在內建構的第一波現代性是現代自由民主指導思想的主要來源,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現代性之上。與之相對,始於盧梭對第一波現代性的批判,經由黑格爾到馬克思發展出來的第二波現代性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指導思想。第二波現代性看到了第一波現代性中的自由和平等僅僅是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即「個人自由」與「法律地位平等」),實質上是不自由不平等,第二波現代性試圖建立形式性和實質性相結合的現代性,真正實現自由和平等(即「共同自由」與「共同富裕」)。建立在第二波現代性之上的社會主義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其目標是實質的自由和平等。現實中的不少社會主義國家卻在不同時期拋棄了第一波現代性的成果,拋棄了市場經濟、憲治、法治、民主、消極自由等原則。本文關於現代性的劃分參考了施特勞斯的劃分,施特勞斯將現代性區分為三波:第一波現代性、第二波現代性和第三波現代性。施特勞斯的第三波現代性實際上是後現代性。凱瑟琳•紮科特、邁克爾•紮科特,第二章〈施特勞斯—現代性—美國〉,《施特勞斯的真相:政治哲學與美國民主》,宋菲菲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27 拋棄了第一波現代性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質上回到了傳統封建社會,其在與建立在第一波現代性基礎上的自由民主國家的競爭中敗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鄧文所說的「西方現代性」是偏重人人自由的第一波現代性,其在否定「西方現代性」同時將第二波現代性也否定了,實際上也否定了「中國法律理想圖景」,這是鄧文不能提出「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根本原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依賴於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認識。中國已經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近代科學革命和民主革命之前,中國文明一直優越於西方文明;鴉片戰爭標誌著西方科學革命和民主革命以後建立的資本主義文明打敗了中國大一統封建主義文明;辛亥革命標誌著中華民族進入了新的文明階段,也就是民主主義階段。我們通常認為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新中國,但實際上辛亥革命就已奏響新中國的前奏。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不同於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新三民主義所提出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等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中國共產黨接續孫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衣缽,進行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最終建立了新中國。袁世凱政權、北洋政府和蔣介石時期實質上是新封建主義的復辟,自然不能算在新中國歷程之中。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6年就進入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
當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旗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主義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基礎上由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過渡後實現的。按照當時中國的經濟水平,是不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這個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出現過。因為舊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都很薄弱,陳獨秀按照教條馬克思主義放棄了領導權,然而工人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最終取得了勝利,實際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上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但政治上領先於資本主義國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徵。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共產黨英明地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政治和法治屬上層建築,因此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補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課,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資本主義階段或者就是資本主義階段,既然是前資本主義或者資本主義階段,那麼就應該在政治上和法治上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這可能是很多人在十八大之前總說「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因而要求啟動政治改革的原因,也是十八大之前主流中國法學界倡導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權利本位論」的根本原因。習近平總書記鏗鏘有力地回應了這些人的誤解:「我們黨始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麼主義。」《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109。28 現行《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個命題可以擴展為普遍性命題「共產黨領導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個命題的論證涉及社會主義國家中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問題,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問題。馬克思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一個側面來劃分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一定的啟發,然而,主流西方政治學對基本政治制度的分類都是以一個國家中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不同為標準的,因此,毛澤東的經典命題「國體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676。29 更具有普遍性。更重要的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建立不符合馬克思的觀點,而與毛澤東的觀點一致。
十八大以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黨中央倡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要復興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偉大地位,卻又被很多中國學者理解為是復興中國古代文化,在他們眼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好像是倒退到封建社會,與自秦皇漢武以來的大一統皇權沒有區別。我們要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封建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然而,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到底有什麼區別,大多數人並不清楚。中國法學界要守新中國之正,需要搞清楚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