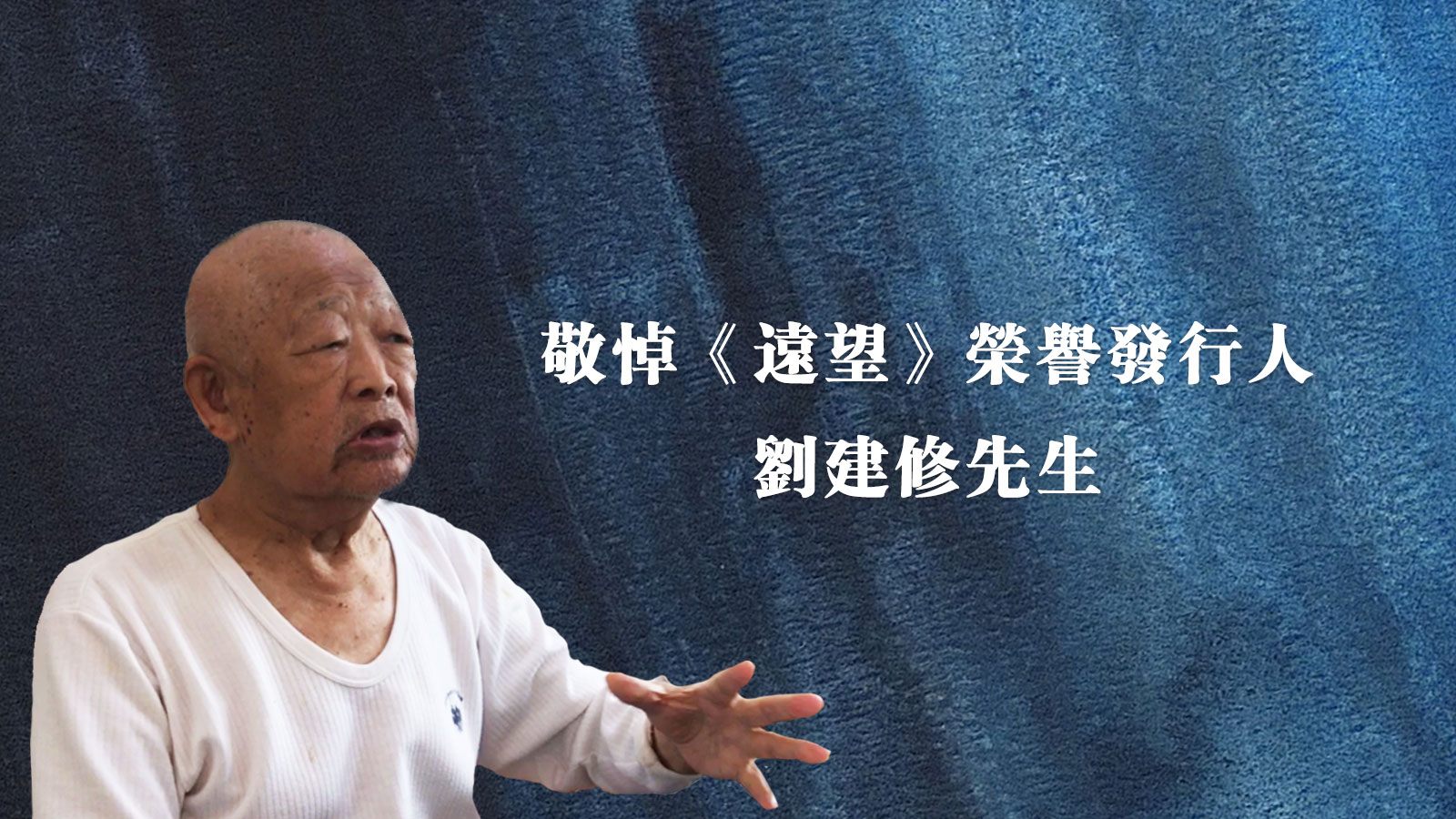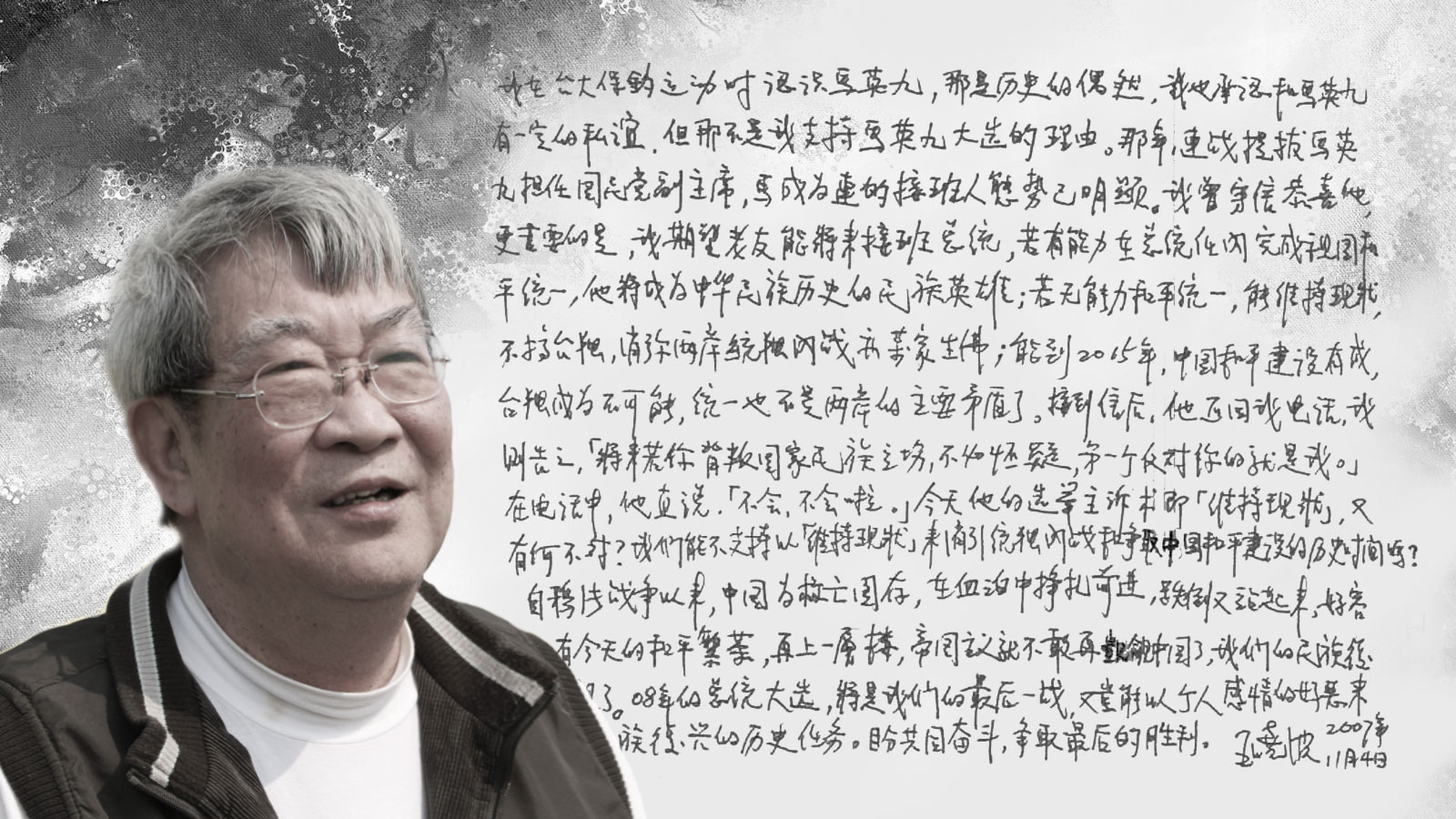捨生忘死的鯤鵬
22歲,劉建修第一次被捕入獄。他永遠記得,自己入獄三天前,已先被捕的計梅真老師來家,設法在隨行特務的監視下給他暗傳指令。計老師說自己一個月前被捕,堅持不住,把組織名單交出去了。表面上,老師說她爭取前來勸其自首認錯,是為免他刑責;實則,藉著送他新婚對枕,老師默默亮出了被拔掉指甲的手指,讓他心領神會,知道老師是已遭長時間刑求,出於被迫。劉建修草草填了悔過書。待來人離去後扯開枕頭檢查,果然沒有字條。他不確定老師究竟是密令他及時聯繫其他同志出逃,還是暗示他不要相信今日所言。由於無法確知組織暴露的程度,為免特務藉他釣魚,劉建修痛苦推敲了兩三天,終究誰都沒曾聯繫。雖然三天後自己依然被捕,但老師還是給他上了最後一課。他終身感激老師的啟蒙,敬佩她高潔的人格,與臨危不亂、視死如歸的勇氣。
從1950年3月7日計老師來家,3月10日被捕、押往保密局南所(臺北市延平南路),再移入北所(延平北路),輾轉關進軍法處看守所(青島東路),然後移監軍人監獄(忠孝東路),直到1951年5月押送綠島以前,是劉建修一生中衝擊最為刻骨銘心的14個月。衝擊,不只因為他很少述及的刑求或苦監,更是因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烈士與難友。
第一次同監的獄友裡,顯而易見「不一般」的一位,後來他才驚訝得知,是與蔣介石頻繁近距離接觸的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吳石進入國民黨軍事機構最高決策層,長期潛伏虎穴。3月1日被捕入獄後,這位在臺地位最高的「匪諜」在狹仄的牢房裡,經常就是盤腿平靜讀書;但凡刑求回來,咬牙挨過幾天肉體苦痛的峰頭了,便又恢復讀書,靜候就義,直到6月10日被處死。吳石的沈著堅貞,深深烙印在劉建修心裡。
晚年,劉建修把自己在獄中或見或聞而深為敬重的人物,納入了他編著的《19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檔案》一書(2014年自行出版,原輯65人;2016年增訂再版,增錄10人),吳石即列為第一篇。由於劉建修忠實的歷史證言,基本符合吳石後來才為人所知的獄中手記,使其在蔣介石國民黨的宣傳刻意抹黑多年後,人格終得昭雪。

劉建修編著《19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檔案》(自行出版)一書的封面
此書記錄了許多為著國家統一、臺灣重建,背井離鄉來臺奮鬥的外省愛國志士。除了前述兩位老師分別來自江蘇和四川,吳石來自福建福州之外,像廣東陸豐人黃賢中,26歲來臺,32歲因「義民中學案」就義,臨刑前絕命詩留下「但願同胞齊奮起,刀斬斧截安足論」、「千萬頭顱作一擲,人民從此享太平」的慷慨詩句。另一位廣東人張伯哲,關押時每天早上起來就把西裝穿好,準備赴死。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留給家人的遺書裡則說:「星星之火,已經燎原」。張伯哲27歲來臺,31歲被槍決;自認已經「聞道」,並相信包括臺島在內中國終能循「道」復興,故能坦然犧牲。這些人,先前在大陸都曾這樣那樣響應抗日戰爭,最後慘死異鄉、屍骨難覓(直到六十餘年後,一部分才在臺北的六張犁亂葬崗被發現),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一貫地愛國。
劉建修也見聞了一些熟悉兩岸的本省籍愛國份子。他們接續早期臺灣抗日菁英,很早就明確認知到:臺灣的命運與中國整體國力息息相關,兩岸本是一家,而且臺灣的問題必須與大陸一起解決才有出路,也才可能真正解決。於是,他們內渡大陸尋找臺灣自救之道。譬如,曾襲擊日殖派出所的李友邦(李肇基),以及曾以教員身分與日殖校長打架抗爭的李媽兜,早在日據中期就相繼離臺內渡,並領導、參與「臺灣義勇隊」在陸抗日;1940年還有鍾浩東(鍾和鳴)和蔣碧玉(蔣渭水的女兒蔣蘊瑜)夫婦等一行人登「陸」,參加抗日。他們看清蔣介石國民黨的問題;黃埔軍校畢業的李友邦尤曾受其多次迫害,但日本投降後,仍首先派員返鄉升起了全臺第一面中華民國國旗。他們畢生為臺灣、為中國奮鬥,所以支持社會主義反帝革命,堅持中國人的事情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他們能清楚區分國家、國號與政權,所以鍾浩東的未亡人蔣碧玉晚年回憶說:「不是國家傷害我,而是當政者傷害我;國家是我們大家的,國家的好壞大家都有責任。」
還有一些出身望族、或受有高等教育的臺籍愛國志士,純粹臺灣本土的社會菁英,原本前程可期,卻熱血投身政治運動。如,來自臺北士林地主家庭的郭琇琮,習醫而一心立志「醫國」,暗組讀書會,二戰末期並擬以武裝響應加速臺灣回歸祖國,不幸被關進日殖監獄、打斷肋骨;光復後仍戮力打抱不平,32歲被國民黨槍決。同樣習醫的吳思漢(吳調和)、曾被臺北帝大醫學部老師譽為「將是臺灣、甚至全亞洲爭取諾貝爾獎的不二人選」的許強,雙雙放棄了學霸的光明前程,分別在人生第26、第37年死於槍下。
劉建修此書也納入一些才華洋溢的青春少年。如,跟隨愛國親戚張棟材(槍決時25歲)的嘉義人蔡志愿,18歲就開始逃亡,21歲高喊著「共產黨萬歲」走向刑場。跟隨黎子松老師(廣東東莞人,槍決時36歲)的新竹女中學生傅如芝,於花樣年華的18歲入獄,10年服刑期間,卻又因獄中「重新參加組織」罪名,24歲被槍決……。這些才子才女原都有著很大的發展空間。
同一家族大量犧牲的慘況,也被劉建修納入書中。如,桃園龍潭的梁雲漢家族,一門六烈,其他多人坐監。……
牢房中,劉建修不斷看到同志臨刑的握別、不久前還同桌吃飯的人消失,聽到送別的「安息歌」、拉人出去的腳鐐聲,心裡暗自計算「前天7個、昨天5個,加起來12個,今天又8個,加起來20個……」,越算越是膽戰心驚,累計到破百,不敢再算下去。他知道其中許多人是明知危險,卻義無反顧投入運動;遭遇非人磨難,卻堅忍不從,用最後一口氣保護運動,選擇了壯烈犧牲。劉建修也知道,蔣介石國民黨罪惡的槍下,幾已從根拔除了臺灣社會的紅色幼苗、斬盡左翼思想與實踐的歷史傳承;最最嚴重的是,他迅速終結了中國在臺灣島上大批既愛國、能力又高的一代才俊,終結了島內致力統一的新生力。
晚年,劉老就曾於訪談中說:「我只是小魚小蝦,只是臺灣中國共產黨底層的一份子而已」,「今天所以由我來講那段歷史,不是因為我曾在臺灣的共產黨組織或左翼運動中做過多少貢獻;我只能說是還存留下來的一個歷史見證者而已」,因為「臺灣真正的大魚都死光了」。
今年5月去看望劉老時,我請劉老描述一下他所認識的「大魚」。他說著說著,幾度老淚縱橫、泣不成聲,不能自已。我知道裡面沒有一滴淚是為自己,一如他在所有自述中,未曾花費多少口舌筆墨於切身遭遇的磨難一樣。哭泣不能自已,是因為他所認識的那些大寫的人,其悲壯無法言傳;而他所受到的感動,同樣無法言傳。我相信,劉老對自己的描述不是自謙之詞,因為劉老親眼見識過那些大寫的中國人,知其悲壯,因為他正是同樣的人,認同其悲壯;只因時運所限,他還倖存人世。
從而我第一次如此確切知道,為什麼中國人創造出「鯤」「鵬」這樣的比喻、「壯懷激烈」這樣的詞彙,來描繪大寫的人。唯鯤鵬能遠望,是螻蟻只貪生。與那些臨難不苟的鯤鵬之士相比,出賣同志的蔡孝乾、李登輝等人不論後來權勢地位多高,也不過螻蟻蟲蛭而已。
可嘆,繼續扭曲了數十年的臺灣社會,今天幾已無人認同那悲壯。
威武不屈的大丈夫
1951年,劉建修等千餘人成為綠島新生訓導處「開業」的第一批人犯。這裡,艱苦勞動、發霉飲食、無端體罰,持續戕害身體;思想教育、小組討論及其發言稿,天天壓抑心靈;爪耙子打小報告、送交二度判刑(後述)、遺世孤島生死無人知曉,威脅始終存在……,在在都是新的考驗、新的凶險。綠島12中隊之外有所謂「第13中隊」,就是政治犯除槍決者外,死後的墳場。
晚年劉老藉難友張皆得的話說:在孤島漫長的牢獄生活裡,要堅持年輕時的理想與志業,也許比在哪兒都困難;此時,烈士們的犧牲,就成為倖存者繼續實踐的精神支柱。(張因「臺南市工委會案」入獄,同案徐國維因拒交名單而被處決;鄭海樹、曾錦堂等人逃獄未遂,遭槍決。)

1962年劉建修從綠島監獄寄回家的照片
槍決,則還送回臺北馬場町執行。1953年7月韓戰停戰協定簽訂前,美國和蔣介石為宣傳共產主義的失敗,便於6月利用戰俘遣返問題,在解放軍戰俘營裡策動所謂「起義來歸」。隨即,為彰顯國民黨在臺感化教育之成功,綠島新生訓導處亦以「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配合響應,要求政治犯效法韓戰「反共義士」寫血書,手臂刺上「殺朱拔毛」、「反共抗俄」等口號。劉建修等人藉口「我們根本沒有『參加』共產黨,怎麼『脫離』共產黨?」拒絕配合。(此前凡承認為共產黨、卻拒絕妥協者,一律慘遭槍決。)獄方挑撥分化、威脅利誘皆告無效,眼看蔣經國巡視在即,便將帶頭的領導份子送回臺灣本島關押。劉建修被視為教唆鬧事者之一,隨同其他四十餘人從此由綠島移監新店安坑軍人監獄,長達7、8年。綠島送走一批高危份子之後,獄方抄房清算整肅,抄出不少問題手記,則又引發了所謂「綠島獄中組織案」。湖南人陳行中,是曾在抗日戰爭淞滬會戰中堅守3個月、後又奔赴中國遠征軍印緬戰場對日決戰的愛國軍官,即因被發現在獄中秘密啟蒙晚輩,送往臺北處決。此外,已移監臺灣本島的高危人犯裡,有人因留下問題手記未及銷毀,也被送判;總計這波由「一人一事」引出的發展組織及不合作事件,兩監又有12人血濺馬場町。大家第一次知道,原來做蔣介石的政治犯,居然服刑期間還能「再判亂」而二度判刑,並且判重、判死。
不過沒想到的是,包括劉建修在內,許多難友出獄後一致認為:入獄前自己只算思想啟蒙;真正的深度學習,實則在鐵窗裡的「獄中大學」才開始。離開綠島後移入的新店軍監,沒有勞動安排,牢房每間25人左右,每個人的出身背景、思想學識程度不同;反正每天從起床到熄燈,有的是挨不完的時間,而牢裡教授、軍官、公務員、醫生都有,各方面人才濟濟,並且一陣子調房一次,於是他們決定積極向學。腦袋方面,這裡有人能把部分《資本論》原文背出,有人能教辯證法、毛澤東著作……。材料方面,他們拿軍監洗腦教材反過來讀,還請家人寄書、或購入新書(後來開放),只要不在禁止範圍,社會史地、理化生物、小說文藝、英語數學……,包括外役看不懂而偷渡著左翼觀點、更新著中國大陸訊息的日文書籍,什麼都有;並趁著每天兩次、每次10分鐘的放風時間,相互交換。以每人兩本書來算,20間牢房(難友並非全由綠島轉入)即有1000本可換著看。於是,每天十幾個小時大家就在房裡安靜讀書,然後會的教不會的,知道的告訴不知道的。你懂唯物論、我說辯證法、他解矛盾論,理論認識就在相互討論中逐步完備;難友廖清纏懂日共歷史,辜金良參加過新四軍可述其所知,江漢津了解臺共源流……,加在一起,便充實了大家對共產黨發展的理解。如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孜孜不倦學會各方面知識、建立起三觀,幾乎讓鐵窗成了共產黨員的訓練班、養成所、進階研究所。包括後來重返綠島,當時獄政管理比較人性化了,也稍可如此。這些曾在鐵窗裡左翼學堂彼此共學、相互勸勉的難友,出獄後便以「老同學」相稱。
獄中有不少只受過日殖教育的人,就是劉建修由注音符號開始教起而學會中文讀寫的,最後要求能寫心得、寫分析,到足可投稿、相互批評。劉建修自己也在獄中學會財經知識,成為其出獄後從事製造業、推展外銷業務的基礎。劉建修主要專注的,則在歷史,中國史、日本史、美國史、世界史廣泛涉獵;特別是,臺灣銀行由日文翻譯出版的大量臺史材料,讓他更加確信歷史的重要性。他說:「一定要懂歷史;現在我們的判斷力,就是以歷史觀點作為基礎。例如我們看了很多中國近代史,看了以後,就逐漸理解中國應該要怎麼走。」劉建修的《臺灣人民的歷史》(文英堂出版社,2007)一書,基本完成於獄中,出獄時特分拆藏於各筆記本攜出。書中有許多引據,部分還是我做臺史研究未曾參考的,非常不容易。
等到1961年綠島送走一大批10年屆期的政治犯,新店軍監的一眾人犯便又遷回綠島。劉建修於其間完成此次的最後4年刑期,1965年3月12日出獄,時年37歲。
由於長期脫離社會,敏感身分又令一般人敬而遠之,劉建修與所有缺乏富裕親族支撐的難友一樣,出獄後處境艱難,求職處處碰壁。所幸憑著一塊不算大的土地遺產,以及堅強的意志力、農家子弟肯幹實幹的精神,劉建修很快得以利用電學基礎,設廠生產燈飾外銷,穩定了經濟基礎。家庭方面,劉建修為免15年的漫漫刑期耽誤元配田氏,1954年即趁移監臺灣之便協議離婚。也可幸,不像很多政治犯出獄後面臨家人的冷遇、指責,甚至家庭破碎,劉建修重新與范日英女士建立起自己的家;雖然不及為父親送終,還來得及回鄉照顧母親。
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劉建修日日觀察在臺蔣氏的走向,時時仍心繫未完成的運動。然而,具體坐過政治牢、被標註了前科的敏感份子,一出獄即被精準納入警特緊盯的對象,不僅「傅道石」(警總輔導室代稱)要聯繫你,轄區派出所也不時前來「打招呼」;員警除對婚喪喜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其他任何聚會、宴請都會主動關切、詢問,甚至強制散會。要想發展組織、進行政治運動,環境只可能更險於往日;知「過」不改,刑責只可能更重於前次。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長達22年(始於1949年10月中共建政)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基本底定,偏安臺灣的蔣介石政權退出聯合國,中國席位由北京接掌。國際上對於國共競爭的態度明朗,由是,島內反蔣意志開始蠢動。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過世隱含的不確定性,更加激活了倒蔣的動能。
一天,難友陳明忠暗自來訪。陳明忠與劉建修於綠島已經相識,新店軍監時期更因曾經同監,彼此對對方的人品、思想,以及組織、領導、行動能力,有了進一步的互信。於是兩位未嘗忘記自己「舉過手」的同志,期約利用劉建修所在地區新竹義民廟中元普渡大擺宴席之機,啟動臺灣中國共產黨的第三次秘密集結,由陳明忠領導,劉建修襄助,將北中南全臺可用的力量組織起來(詳見本期龍紹瑞〈記劉建修談屢仆屢起的臺灣地下黨人〉)。可惜,由於立委黃順興和女兒黃妮娜在未與陳明忠充分協調的情況下,兀自冒險行動,並於日本暴露形跡,致使特務直抄陳明忠臺北住處,據抄得的錄音帶、購書收據,找到錄音帶源頭陳金火所連結的「圖謀暴力叛亂」一眾人等,以及向書商三省堂李沛霖購書的劉建修等一眾日文「匪書」買家。本案終因國際人權組織介入,「主犯」陳明忠、陳金火雙雙從鬼門關前路過,死刑改判15年,已是不幸中的大幸。
聯絡老同學才剛開始,什麼都未發生即胎死腹中,換來十數人再次的牢獄之災,第三次集結可謂重挫。
劉建修從7年刑期改判交付感化3年;但連同上訴期間計,1976年這第二次被捕入獄,前後實達5年之久。關進土城生教所(「臺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的簡稱。後,改稱「仁愛教育實驗所」),劉建修遇上了淡江大學的蔡裕榮(1977年「臺灣人民解放陣線案」)、成功大學的吳俊宏(1972年「成大共產黨案」)等新一代的左翼青年。白恐多年嚴控下,臺灣新生代其左翼思想的淵源、行動的目標與組織能力已大異於前,兩代間出現一些斷層,於是劉建修選擇性地在其間進行了世代傳承的啟迪教育,直到1981年再度出獄。
再出獄,劉建修已經53歲。所幸第二次獲刑未如陳明忠、陳其昌那樣伴隨財產充公,加上妻子強韌幹練,獨力扛起家庭和事業雙重重任,生產外銷持續運營。這個辛苦維繫下來的經濟基礎,也就成為其日後長期勉力支援統運諸多項目的根基。(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