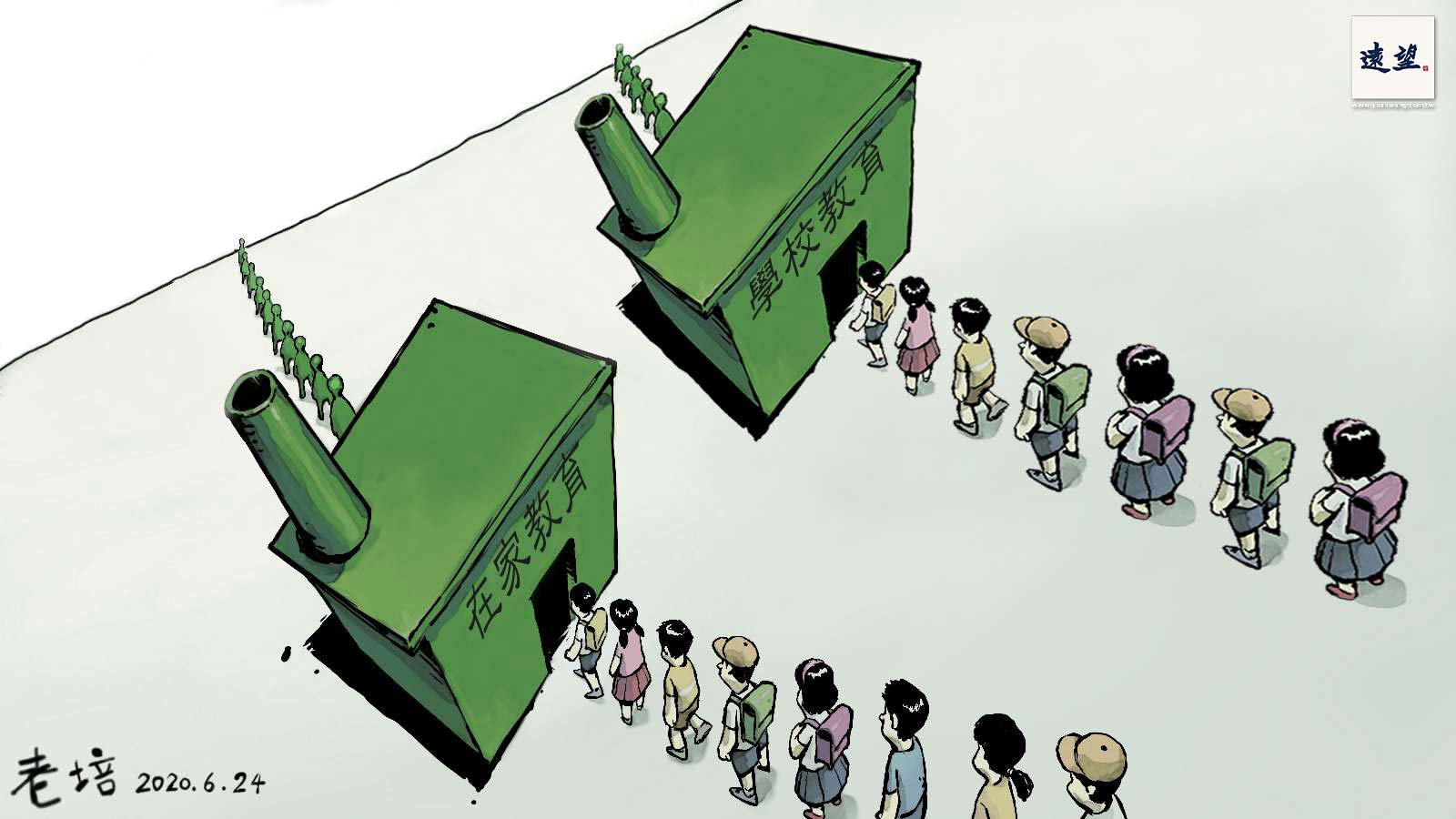今年是中國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也是臺灣光復70週年。說起抗日,當然要提日本侵華,而日本侵華,實又始於1874年的臺灣「牡丹社事件」。從此日本一步步布設了從琉球而臺灣,從臺灣而全中國的侵華大計。此所以唯待全中國抗日勝利了,做為中國一部份的臺灣也才同時有了光復之日。
牡丹社事件的幾個關鍵當事國,除了中國、日本,還包括美國。昔日日本的戰略思考,乃當今美國所謂「第一島鏈」這個地緣政治的雛形;而其切入點,則是中國傳統「天下觀」裡的中土與邊藩關係。
天下秩序中的中土—邊藩關係
自周(公)孔(子)思想建立起「為政以德」、「王道天下」這個統治權正當性以後,中國歷代就或多或少體現著對內講究民本、對外標榜各族群和合共存的政治傳統。以「華夏」、「四海之內皆兄弟」彰顯諸夏並存的「天下」秩序,以「近悅遠來」、「協和萬邦」做為明君英主追求的統治目標,即其部分表徵。
而隨著「天下」由周的封建體制演進到秦漢以後的中央集權,做為政治與文化核心的中土、「中國」,遂由周王直轄的王畿,擴展至皇帝相當程度有效統御的範疇,而天下秩序中的邊藩,也由「以藩屏周」的封建諸國,轉變為中土四圍的各民族居地。「藩」字儘管逐漸簡化為「蕃」、「番」,其借以指稱中土周邊族群則始終如一(換言之,「番」字原無貶義)。
於是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歷朝中土與各邊藩之間,只要彼此和睦,則其關係依據親疏遠近,可以是從直轄、(各種程度的)半自治、自治,到(各種頻率的)朝貢、甚至全無互動的這個光譜中的任何一種,形式不一而足;對許多地方、民族而言,天高皇帝遠,天子不過是天下秩序裡的共主。因此,中國所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在仁義禮智的普世價值下融入的血緣越來越多,卻又保留著活潑多元的族群色彩;另一方面,邊藩民族一旦入主中原,卻也爭相代表這個天下秩序裡的普世價值。Martin Jacques與張維為稱之為「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而迥異於西方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同時,這個「天下國」沒有具體、固定的疆界,而有別於西方的主權國家。
清朝將臺灣納入中國的大一統版圖以後,對臺灣原住民採取的政策,便是上述傳統的延續:一方面將儒化程度高的平埔族與漢移民等同視之,納入直轄,一方面對其他原住民依儒化程度高低予以區分,並據以設立番界以保護其半自治或自治空間,或設通事以利溝通。


近年臺灣有些人既不諳歷史,又崇洋媚日、自輕自賤,竟謬稱臺灣溫泉的開發、林礦的大量開採,都要歸功於日據時期日本科技文明或殖民制度的高明有效。殊不知不但原住民早已活用許多天然資源,而且清政府未嘗在臺大規模開發山林資源,係因其早自臺灣納入版圖之初,即已明令保障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可見清朝乃「不為也,非不能也」!

臺灣考古發掘與原住民關係圖譜。由下而上,表示時間上由早而晚;由左而右,表示空間上由北而南。來自底部的箭頭,表示直接來自島外的移入者。
長期各自為政的臺灣原住民社群
臺灣的「原住民」,有先來後到。其最早來者,與考古發掘距今四五萬年前的長濱文化、網形文化之間,或與距今六七千年至四千多年前的大坌坑文化之間有無承續關係,已不可考。而最晚進入臺灣地區的達悟族,時間在距今五百年前,甚至晚於元朝即由福建永春、南安遷臺的漢民或某吳姓支派(根據族譜)。究其來源,則有所謂的南島語族,也有來自於東亞大陸者,如芝山岩、圓山、十三行文化的住民都是。
所以,何謂「原住民」?臺灣位居歐亞板塊東亞大陸棚邊緣這個客觀事實,使得漢移民和許多原住民一樣,生活圈很早就無甚技術障礙地自然延伸到了臺灣(起碼是局部的臺灣),而且明鄭以前,漢人移入形式與性質主要(雖非唯一)是民間而零星、和平的,意在維持交易或謀生。當荷蘭人帶著國家授權使用的槍砲與基督教聖經進駐南臺灣時,早已熟悉閩南語「麵線」、「豆油」的南部平埔族,卻排斥荷人到不惜冒死設陷報復,如荷蘭第一任大員長官宋克之死即是;後來聽聞國姓爺即將來臺,便又不願出席荷人主持的地方會議,甚至引頸期盼國姓爺早日趕走荷人。總之,「原住民」一詞,用於統稱歷來以部落或部落聯盟為單位而各自為政、認同互異的部落社會,是無效的,也不能用來排擠自然移入的各族群(包括早期漢移民在內)和平居住權之正當性。
《臺灣府志》等清代臺灣諸方志中所謂臺灣向為「無主之地」,此「主」亦非所有權人、使用人之意,而是傳統「共主」、「作主」的「主」,即決策、領導之意。因此,臺灣長期為無主之地,乃歷史事實,其概念來自中國多元和合共存的天下觀,迥異於西方傲慢的白人沙文主義;而直到清朝,臺灣住民(包含原住民)才第一次有了共主、一致的國籍。此所以方志既說「臺灣向為無主之地」,又說「臺灣自古屬於中國」,毫不矛盾。而儘管番界之外、「後山」之地,乃清廷並不直接介入的「化外之民」活動的「化外之地」,然其一旦有事而求助於「共主」,則清廷只要力所能及,仍會派員平定,然後退出。例如1816年前後的「郭百年」事件,臺灣總兵武隆阿逐出越界侵墾的漢民、拆毀其居住防禦工事,然後地歸番社、立碑重申墾禁,即是一例。
日本的大國夢與片面最惠國待遇
日本想與強鄰中國分庭抗禮,早自六、七世紀之交聖德太子攝政的推古女皇時代,日本開始創造「天皇」及其神話,其對華國書中自稱「天子」而不同於稱王的朝鮮、越南,即已初露苗頭。此後,以日本為中心的翻版「夷夏」觀念逐步確立。至豐臣秀吉以天皇征夷大將軍之姿叱吒日本時,甚至揚言遷都北京,「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于億萬斯年」,取中國而代之。腹地相對狹小、資源相對匱乏的島國日本,其對華情結及大陸夢,簡直可用俗話「羨慕,嫉妒,恨」來一言以蔽之。豐臣雖兩度妄圖藉朝鮮、臺灣互為犄角以挾制中國,都告失敗,抑鬱而終,但島國日本的大陸夢,仍遺傳到了繼起的德川家康、直至「大政奉還」後明治以降的日本帝國。

屏東高士佛社排灣族原住民,是日本侵華最早的受害者,也成為1910年日本對國際展示其帝國主義事業的樣板。
大陸夢未及成真,1853年美國黑船轟開日本德川幕府以來的鎖國令,次年日美簽訂《日美親善條約》、即《神奈川條約》,隨後英、俄、法等國也起而效仿,紛紛與日簽訂「親善條約」,而其神髓幾乎就複製了1840年的中英《南京條約》——日本被迫開埠通商,列強對日取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立租界等各種特權。
中英《南京條約》,是近代以來中國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訂約之時,除了國家實力的現實因素外,久於以德服人的政治傳統,加上未曾真正面臨過「亡天下」的威脅,中國即使明末以來已與西方國家接觸了兩百多年,仍始終猜不透列強腹中繼續醞釀的伎倆。在此背景下,中國卻首先就被迫簽訂了片面最惠國待遇,讓任何一國新從中國取得的有利條件,他國都可要求「利益均霑」。從此,既促成列強協同對華分進合擊的合作關係(例如,才因歐洲克里米亞戰爭生隙的英法俄三國,對華卻合作扮演黑白臉,藉由英法聯軍之役迫華簽訂新約),並每欲借小事以擴大,從而也使中國面對列強生事時投鼠忌器,每欲大事化小。而這又反過頭來鼓勵了列強,讓中國難以掙脫其蠶食鯨吞(直到二戰結束,中國做為戰勝國之一取消不平等待遇為止)。後來,日本在台發動牡丹社事件,後人每譏嘲中國打贏卻簽訂喪權辱國的《中日親善條約》,間接承認了日本對琉球的宗主權;其實,片面最惠國待遇才是使中國急於謀和的真正原因。
然而日本雖也與西方列強簽有片面最惠國待遇,卻因地緣政治,改變了這個宿命。
地緣政治與美日合作
就在美國轟開日本國門的1850年代前後,日本已有人從蘭學(即西學)中吸取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並應用於解決日益嚴重的外患問題。對於相信王道天下價值傳統的中國人來說,認同弱肉強食原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毋寧只是認識西方的一個窗口;但對日本而言,卻是毫無捍挌的學習對象。例如幕末集「海外發展論」之大成的左藤信淵(1769-1850),即力主經由「混同世界,統一萬國」,躋身西方人眼中的第一等國家、即吃人的國家;而其方法,則是檢軟柿子吃、「自弱而易取始」——從受清廷保護而人口稀少的「龍興之地」滿州入手,切斷中土與朝鮮的連結,「則朝鮮、支那,皆次第可圖矣」。及至「黑船事件」發生未久的1850年代末,眼看英法即將效法美國取利於日本,鹿兒島藩主島津齊彬也說:「法既得志於清,勢將轉向而東。先發制人,以今日之形勢論,宜先…取清國之一省,而置根基於亞東大陸之上,內以增日本之勢力,外以昭勇武於宇內,則英法雖強悍,或不敢干涉我矣。」而其方法,吉田松陰(1830-1859)在其繫獄之作《幽囚錄》中「論保日之道」時,進一步發展:「北割滿州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以制華;1870年代之初成富清風的〈台灣地方覺書〉更予以完備:「台灣島位於琉球番之西南,實吾皇國之門戶也。如果該門戶不能堅守,出則無法控制西南各國,入則無法捍衛皇國」。於是「滿州—朝鮮—日本—琉球—臺灣—呂宋」這條從豐臣秀吉以來即隱約成形的制中外環,即20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口中的「第一島鏈」,此時戰略完全成熟。而其南向發展的第一步,即在併吞琉球。
然而綜觀日本的大陸夢、環中國以制中的戰略,若非美國為其提出理論基礎(「東亞文明月彎」概念、「無主之地」論,後述)、鋪平道路,怎可能成真。而其間的關鍵人物,就是1850年代巡曳於太平洋西岸的美國海軍提督培里(Matthew C. Perry),以及一度做為美國廈門領事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又名李讓禮,1830-1899)。
培里在轟開日本國門後,接著曾藉由營救在臺遇難美商之機,派員訪問了基隆港,還強占了打狗(高雄)長達7個多月之久。培里積極建議白宮佔領或購買臺灣。然美國不但擴張起步晚於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國力也明顯低於他們,而美國國內還因黑奴解放問題逐步陷入南北戰爭,使其無力並無心於在歐洲列強已深入經營的臺灣等地與之正面衝撞。儘管如此,美國已清楚知悉臺灣做為中國的一部份、東亞的外環,因此而對箝制中國、控扼東亞所具有的地緣價值(並且至今仍然有效)。於是等到南北戰爭結束,美國即加緊展開臺灣對美國在亞洲的戰略佈局了。
李仙得,從美國南北戰爭中受傷退役的獨眼將軍,1866年出任了美國駐廈門領事。次年美國商船「羅發號」(the Rover)觸礁沉沒於台灣東部外海,而其生還者在登陸琅���(今屏東)後卻遭土番殺害時,李仙得即擔任美國與清政府交涉的代表。此時清廷為洋務分身乏術,對邊疆已感力有未逮,故乃以琅���位屬「生番」地界,朝廷不宜介入「化外之地」為由推託,期以讓美國知難而退。不料李仙得決定於1869年親自來臺交涉。此後在英人走私臺灣樟腦引發的糾紛裡,以及無數的教案、商務糾紛裡,都有了這位獨眼將軍的身影。
李仙得從擔任廈門領事以來累積的中國經驗,讓他瞭解到傳統中國的中土—邊藩關係裡不同於主權的宗主權,以及不平等條約裡「領事裁判權」對列強、中國分別發揮的作用。而李仙得此番進入琅���與18社總頭目卓杞篤談判取得的協議,及其能用閩南語以及部分土語而與18番社溝通的語言能力,又使李仙得迅及被視為「臺灣番界」通、中國通,並對所經之地完成了完整的測繪。而清廷有關於「無主之國」、「化外之地」的說詞,雖僅是一時的推託,更引起了李仙得的注意,後來並援引利用。
布局
與此同時,在李仙得的建議下,1871年美國駐日公使德朗(Charles E. De Long)呈文國務院,主張「日本與中國不同,美國應歡迎日本成為盟友;與中國有衝突時,文明諸國應視日本為一夥伴。」對於西方國家來說,直接統轄東亞地區,難免鞭長莫及,於是英美等國開始把日本從被掠奪者,拉為協助自己壓制東亞的合作夥伴。1872年李仙得遂辭去廈門領事之職(之前安排了許多假動作),並以返美過境日本橫濱為由,在美國政府的授意下,經美國公使引介而與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有了接觸。
明治維新啟動後的日本此時,內有大量士族失業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壓力,外有對外擴張以免淪為列強魚肉的強烈願望,又適逢琉球國宮古島、八重山漂民在臺灣「化外之地」遇難未久。李仙得乃以其參與處理羅發號事件的經驗,提醒日本政府「臺灣雖受清朝管轄,但其政令不行,對人民也不能保護,既無有效統治之實,乃一無主之地,日本可趁此良機佔領台灣」。於是一方面,李仙得提供給日本相關訊息,包括詳細地圖,協助雇用外籍軍人、承租船艦、購買軍火的保證,以及明明與遇害事件無關、卻具有戰略意義的攻台路線之規劃(包括藉由阻隔澎湖以快速切斷臺海兩岸的聯繫),給日本侵臺以具體而完整的協助,並促使明治政府於1872年私自強行廢止琉球王國,改設琉球藩,以令制國的地位將其置入鹿兒島縣,以為日後日本以保護「國民」(當時琉球同時向清朝和日本朝貢)、質問生番為藉口而出兵臺灣鋪路。
另一方面,李仙得在1873年他給日本的備忘錄中,最早提出了日本做為「東亞文明月彎」的概念:「日本、朝鮮、琉球、臺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臺灣用兵既是應然、也是必然。」這不但為日本出兵臺灣奠定了基於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這個原則的理論基礎,蒙蔽國際視聽,而且由「文明日本」領導的「東亞文明月彎」概念,也是此後日本打造「大東亞共榮圈」的起手勢。一如《後藤新平正傳》一書所述,「這個年輕的帝國,正在開始實施由李仙得忠告而發起的堅固的新國策——大陸政策,即北起樺太(即庫頁島)、南到臺灣,由一連串島嶼完成對支那的半月形包圍,更要控制朝鮮和滿洲,否則就無法保障帝國的安全,控制東亞的時局。」
結論
美日首次聯手制華,始於合作侵臺,而侵臺始於協力發動「牡丹社事件」。其所以如此,日本主要是基於其腹地狹小、資源有限,因而後援無力,無法獨力完成擴張夢想;美國主要是因為地理區位上距華天遙地遠,國際實力上受到他國先馳得點的干擾,而不便直接涉足的現實。美日聯手、相中臺灣,則都是地緣戰略的考量。美日聯手侵華,並非哪一方誘導另一方所致,而是彼此順藤摸瓜、相互利用;美、日對這段歷史的任何「脫罪論」,都是誤導、隱瞞。
一方面,美日聯手侵華的歷史自此一直發展至今,中間除了太平洋戰爭短短的四年因為美日資源競賽而中斷之外,戰後美日立刻又或暗或明地迅速恢復了同盟關係,昔日為日本擴張主義服務的「東亞文明月彎」,更已幻化為今日美國壓制中國、控扼西太平洋的重要戰略——環繞東亞的「島鏈」。
另一方面,在當今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裡,昔日由中國天下觀積累而成的中國多民族國家,繼續受到西方以人權與主權觀念挑戰中國的族群關係(包括原住民),並以此做為動搖中國內部凝聚力、支解中國的下刀處。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但美國總統歐巴馬和國務卿克里於9月2日發表的紀念二戰太平洋戰爭結束70週年的書面聲明裡,竟然著重提及美日和解,強調「美日新關係時代開啟」,卻沒有提及中國。美國就像昔日一樣,願意繼續充當日本胳膊往外彎、躋身東亞高位的底氣,以聯手壓制東亞文明,對此,我們不能不知。
此外,臺灣做為中國的一部份,臺灣的命運是中國的縮影,這是自然,也是必然。在乙未割臺兩甲子、臺灣光復70週年的今天,我們必須知道唯待全中國的抗日、抗美勝利,才有臺灣不再受到美日干擾的日子,臺灣住民也才真正能有昂首闊步的人格尊嚴。